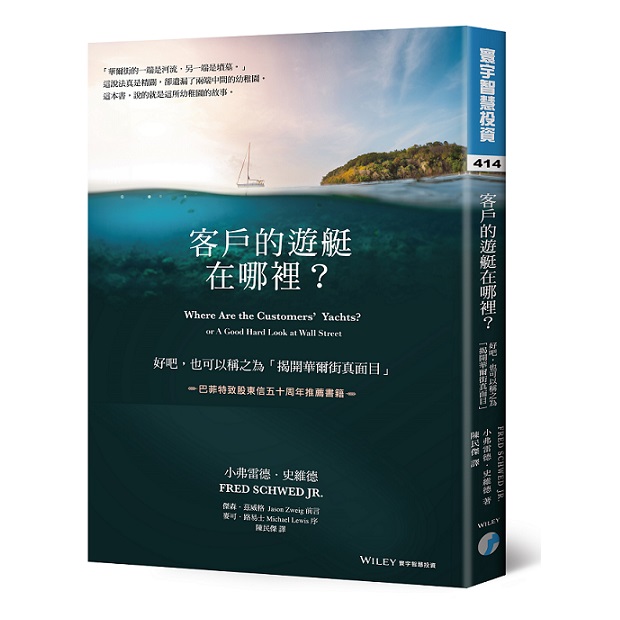
客戶的遊艇在哪裡?好吧。也可以稱之為「揭開華爾街真面目」
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 or A Good Hard Look at Wall Street
-
定價
350元
-
優惠價
88折308元
-
會員價
77折270元
-
加贈點數
0點
- ※購書免運門檻,大宗購物流程,詳見"常見問題-財金書城相關"。
◆巴菲特致股東信五十周年推薦閱讀書籍、波克夏股東會多次點名必讀經典
◆「這本書是有史以來最有趣的一本投資書籍!」、「本書的智慧與幽默真正無價」——股神巴菲特親自推薦
◆財經作家雷浩斯、《大賣空》作者麥可.路易士、《智慧型股票投資人》總編傑森.茲威格專文強力推薦!
你看,那些都是銀行家和經紀商的遊艇。
鄉下人天真地問:「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是什麼樣的酸言酸語,能讓巴菲特和投資界數十年來如此愛不釋手?
是什麼樣的脫序失言,能把全世界證券業者從頭到尾一次得罪個夠?
讓在股災中虧一大屁股錢卻從此躋身暢銷作家的「專業交易員」小弗雷德告訴你,什麼是投資界不敢說卻不吐不快的真相!
「華爾街的一端是河流,另一端是墳墓。」
這說法真是精闢,卻遺漏了兩端中間的幼稚園。
這本書,說的就是這所幼稚園的故事。
【作者警告】
這本帶有恐嚇意味的書,如果再版之後導致全世界證券市場暴跌,我不會推拖。
我會大方承認那是我幹的!
不過,我也對所有因此賠錢的人保證,我的歉意絕對出自真心誠意。
【精采試閱】
在極度恐慌的一九二九年,有一家投資信託公司的董事會召開了一連串的緊急會議。
某個深夜,這些臉色蒼白、精神萎靡、躊躇不定的男人們圍坐在桃花心木的大會議桌前,極力避開彼此的眼神。
他們的一切信念都被粉碎了。
突然,其中一人說話了,語氣平靜而堅定:
「我們無法得知道情況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某某某(他說的是當時一支熱門藍籌股)已經跌到接近兩百元,而兩個月前的價格是三百五十元。
這聽起來有些荒誕,但我覺得這支股票有可能下探一百五十元。
如果到時候我們能夠以一百五十元買進一萬股,那難道不是千載難逢的便宜貨嗎?
這也可能不會發生,但我們難道不該好好準備迎接這個良機嗎?」
這個堅定有力的發言,即刻讓整個會議室充滿熱切的希望之光。
討論頓時熱絡了起來,原本蒼白的面頰也有了血色。
「記下來。」其中有個人對著那個二十歲的委託單專員說,
「下單,以一百五十元價位買進某某某一萬股,設為取消前皆有效指令。」
年輕人聽從指示,身子傾前在紙上做記錄,
但此時噘起了嘴,發出了極微小卻明顯帶著輕蔑的聲音;
他們聽到了,年輕人嘴裡說的是:
「有夠鳥的。」
瞬間每個人的信心都消失了,不知不覺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討論,最後那個提案被推翻。
向我敘述這起事件的人說,這個年輕人的嘟噥估計為投資信託公司保住了七十五萬元,
但不會有人向他道謝,因為沒有任何人敢承認那筆毀滅性交易單的取消與他有關。
【名人推薦】
本書可以讓你從中學到不少金融投資業中的人性荒唐,對於從來沒有買賣過股票的旁觀者來說,這些荒唐事真不該出現在現實生活中。——雷浩斯,價值投資者、財經作家
這本書是有史以來最有趣的一本投資書籍,他用輕鬆詼諧的方式傳遞給讀者許多非常重要的投資知識。——華倫.巴菲特
當我翻開了第一頁,就忍不住把整本書讀到最後。史維德用看似簡潔輕鬆的口吻,捕捉了整個投資產業的瘋狂本質。——麥可.路易士,《大賣空》、《魔球》作者
本書是描寫華爾街生態最有趣的書之一 。——珍.布萊恩特.奎因(Jane Bryant Quinn),《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一部令人捧腹大笑的經典終於再版,證明了歷史總是一再重演,只是換了一批初入虎口的羊群名單。——邁克爾.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史維德的書籍在出版五十五年之後仍然讓人著迷,華爾街唯一的改變是電腦已經取代了鉛筆和紙。
然而,一切基本原則依舊完全相同,若投資人相信財務顧問能帶給他們更好的生活,我想失望的人絕對是前者。
——約翰.羅斯夏爾 (John Rothchild),《笨蛋和他的錢》(A Fool and His Money) 作者、財經專欄作家,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
FRED SCHWED JR. 【小弗雷德.史維德】
身為一名「專業交易員」,他在一九二九年股災時虧了一屁股錢並離開了市場。
幾年後,他出版了一本暢銷童書《古怪小男孩》(Wacky, the Small Boy),然後,接著寫下膾炙人口的《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推薦序: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這本一九四〇年代的美國好書,它的年紀應該比許多讀者的年紀都還大,並隨著時間的流轉來到了台灣的出版市場上。作者在一九五五年版本的前言說:「出版十五年後仍被記得的書實在不多。」他可能沒想到,到了二〇一七年仍有人記得他的書。
本書的書名來自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鄉下人去到紐約金融區,嚮導對他說:
「看,那些是銀行家和經紀商的遊艇。」
鄉下人天真地問:「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這個簡單的故事點出了一個基本問題:
「金融業有沒有為他的客戶帶來附加價值?」
金融業(或者財富管理業)是個很奇怪的地方,他們對有錢人的客戶提供建議,但是這些建議不見得能讓客戶賺到錢,而只是讓金融業賺錢(如果你想要真正有用的建議,可以看本書第八章的一八一頁:一個小小的絕妙建議)。對於這樣的矛盾點,有些人會以痛批的方式陳述其中的貪婪,但是本書的作者小弗雷德・史維德卻用幽默的方式來展示,彷彿是荒謬舞台劇中的串場人,用華爾街歷久不衰的名言,道出大家心中不敢說的實話,而這些實話不分古今中外,皆可適用。
本書可以讓你從中學到不少金融投資業中的人性荒唐,對於從來沒有買賣過股票的旁觀者來說,這些荒唐事真不該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對於已經踏入市場的人來說,卻會把荒唐當作日常生活的風景,套句作者的話:「那些蠢事就像是洶湧的密西西比河,終年澎湃。」避免掉入河中的方法,就是事先以旁觀者的心態用本書來預習一番。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總是會想到《股票作手回憶錄》那個年代的用字遣詞,在感受書中的幽默智慧之餘,也讓我們在過去的股市歷史之旅中遊走一圈,體察人性的變與不變,樂趣和辛苦,還有用金錢也買不到的經驗。
——雷浩斯 價值投資者 財經作家
推薦序 雷浩斯
新版前言 傑森.茲威格
序 一九九五年版 麥可.路易士
作者前言 一九五五年多頭市場版
1.引言——「小詩人輕聲一咳。」 040
金融預測的有效性 046
熱愛預言 052
在牛市裡欣喜若狂 056
2.金融家與預言家 058
大銀行——華爾街的金飯碗 059
一些小資本家 062
華爾街人的思想果實 067
華爾街語義學 068
圖形分析員 070
關於待遇的問題 074
錢難「賺」 076
繆斯遺棄的藝術 078
一個小小的性向測驗 081
3.打不死的客戶 086
客戶百百種 087
如何爭取客戶 088
保證金 091
水壩潰堤時怎麼辦? 094
一些個案歷史與診斷 097
炒錢為業 100
4.投資信託——承諾與績效 104
切莫重蹈覆轍,讓專業的來 107
致勝點在哪裡? 108
為地獄鋪路的投資信託公司 114
何謂「最好」 115
價值七十五萬元的嘟噥 118
說說好話 119
夢幻投資公司 121
5.黑心肝的放空者 124
辯護 127
另一種辯護 129
趕走了熊,然後呢? 132
空頭襲擊 137
6.漫天喧嘩的選擇權遊戲 142
選擇權大概是個什麼東西 144
為賭博行為辯護 148
小心陷阱 150
7.逝去的「美好」時光,以及「偉大」的舵手 154
大老們的智商 156
透視投機 160
淺談機率 163
親愛的,你總會有摔跤的一天 165
「他們」 166
作手 168
裝著硬幣的銀碗 170
8.關於投資,問題總是太多,答案總是太少 174
有錢人的煩惱 176
一個小小的絕妙建議 181
價格與價值——封特別的市場快訊 183
現金才是長期投資 186
你追求哪種生活方式?——這已然是個哲學問題 188
9.改革——種種是與不是 192
錢被偷了?還是丟了? 193
不討人喜愛的專家 196
監管的眼界與限制 200
這不是結論 206
【關於作者】 210
關鍵字:寰宇出版/ FRED SCHWED JR. 【小弗雷德.史維德】/ 陳民傑
精彩試閱
新版前言
二〇〇〇年一月的一個晚上,我離開位於曼哈頓五十街與第六大道交界處的辦公室,攔了一部計程車。司機開了一小段後,在紅綠燈前停下。稍後,四個西裝筆挺、繫著領帶的男子大步走向街道。其中一個敲擊駕駛座那一面的車窗。司機把車窗打開一道小縫,然後這位「優秀青年」開始吼叫:「我們要到四十九街跟公園大道街口。」——這離我們當時所在的地方只有四個街區的距離,步行個幾分鐘就到了。「我有客人了。」司機說著,順手把大拇指指向後座的我。「叫他下車,」這一臉跩樣的年輕人說,「我們給你一百元。」他可不是開玩笑的——話一說完,他從車窗縫隙把一張一百元鈔票塞到司機眼前。「我不能這麼做,」司機拒絕他,並且把錢推回去。這時候綠燈亮起,司機關上車窗,油門一踩,我們就像兩個少女,急著逃離匈奴大帝阿提拉的帳篷。
這場奇異的計程車劫持劇在我心裡縈繞了好幾天。我想到有關多頭市場、金錢,以及曼哈頓的種種,但我從這個事件似乎還聯想到一些什麼東西,只是我一時說不出來。然後,一個星期過去了,「客戶的遊艇在哪裡?」(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這幾個字卻毫無預警地突然冒現在我的腦袋裡;我馬上在小弗雷德.史維德(Fred Schwed, Jr.)的著作裡找到這一段文字:
在一九二九年,每個工作日早晨駛進紐約市賓夕法尼亞車站的列車都附有一個豪華車廂。列車停站後,原本正在玩著橋牌、閱讀報紙,或相互較量財富的百萬富翁們依序從車廂前面走出來。車門旁放置了一個裝有五分錢硬幣的銀碗,需要硬幣搭地鐵進城的人都可以自取。他們不需要拿什麼來交換——這不是錢,而是像為客人提供牙籤那樣的小小便利,人人可免費取用。畢竟,那也不過是五分錢。
一九二九年十月驟然而至的大崩壞,有各式各樣的解釋。我比較喜歡的解釋是:憤怒之神耶和華剛好在十月看到了這個銀碗。他突然一陣惱怒,而這是可以理解的。於是,他一腳踼翻了美國的金融體系,讓這個裝有免費零錢的銀碗永遠消失。
再次重讀時,史維德的這一段文字確實擊中我的思緒:多頭市場的高昂情緒已經漫天遍野,原來,金錢早已再次淪為某種「小小便利」。年輕人寧願花個一百元打發一個陌生人,也不願意走過四個街區。史維德的文字把我從自身遭遇的憤怒中拉出來,再把我拋入一陣寒顫之中¾¾他似乎讓我預見了股票市場即將發生的事。我知道,耶和華隨時可能到來,並扯去那一張一百元鈔票。
我的預想沒有錯——或者應該說,史維德說得沒錯。短短不到六週之後,納斯達克指數(NASDAQ)開始暴跌;往後的兩年半之中,這個指數跌剩下高峰時的四分之一。把百元鈔票當作用過的紙巾般那樣揮灑,原來代價這麼大。
史維德那則有關零錢碗的奇聞軼事竟成了預言,這並不是巧合。讀著這本經典小書時,你會一再地發現史維德的字裡行間透露出某種底蘊,那是從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孟肯(H.L. Mencken),到湯姆.萊勒(Tom Lehrer)、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等等偉大創作者與表演者繼承的幽默傳統當中所蘊含的思想特色:對理想的熱忱、對正義的渴望,而且總是因世界脫離其原本該有的樣子而憤怒不已。史維德是個幾乎不會將憤怒形於顏色的紳士——但他的悲憫之情顯露無遺,而他的警語幾十年來仍在空中迴響。
從史維德的年代一直到今天,華爾街的一切看似時過境遷,但實際上其核心的遊戲卻從來沒有改變。散戶投資者仍然處於食物鏈的最下層,就像一團浮游生物漂浮在大魚爭食的海洋裡。華爾街的改變微乎其微,以至這麼多年過去了,史維德的揶揄嘲諷讀起來竟讓人以為是預言:
◆在二〇〇三年的共同基金弊案中,基金經理被揭發違反他們自己的交易規則,以謀取更高的佣金收入。史維德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描述,即預示了這群人的面目:「每一天閉市後,他們便把所有的鈔票往空氣中撒去。所有黏在天花板上的錢即歸客戶所有。」史維德這段話為客戶提出警告:你必須像看守一隻鷹那樣地監視著你的基金經理——別對他們所說、所做的照單全收。在這醜聞揭發之前,大部分投資者即抱持著這樣的態度。
◆有些人對企業的財務報告投以完全信任;對於諸如安隆(Enron)或世界通訊(WorldCom)之類的大公司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從來不予質疑。史維德說:「會計甚至不是藝術,而只是一種心智狀態。」如果他們謹記著這句話,或許就會看得更透徹。這句話也提醒了我們:你若不懷疑,你就不可能是個投資者。
◆倘若你一心只惦念著股票價格,對該企業的價值卻一無所知,那麼你也不算是個投資者。一九九〇年代末期,許多交易者對他們買賣的股票根本不做任何研究,眼中只有股票代號如CMGI、DCLK、WBVN,而且只關心價格是否往上走。公司的經營者是誰?公司生產什麼?業務是否獲利?——只要股價上漲就好了,誰會在意這些事呢?史維德的時代也一樣,交易者忽視企業狀況,眼中只有股票代號與報價。他們的下場就是徹底毀滅;數十年過去了,新一代交易者的命運也一樣。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史維德那成對的定義:投機指的是把小錢變大錢的嘗試,這種努力通常會失敗。投資指的是防止大錢變小錢的嘗試,這種努力通常會成功。
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想要快速致富的人還是跟史維德那個年代的人一樣,堅持自稱為「投資者」——但他們明明就是投機客。根據史維德的估算,他們的失敗機率大約為二十五比一,我認為這個數字相當實在;而且,今日的電腦科技與線上交易系統縱使再進步,也絲毫不會增加他們的勝算。
綜合以上所述,史維德的作品確實能媲美許許多多更為嚴肅且詳盡的指南,讓你了解投資世界的荒唐與種種陷阱。畢竟,學習如何更明智地投資,過程往往並不怎麼有趣。有時候,某一本書能夠引發你的思考;有時候,你會從中有所學習。但是,從來就沒有任何一本有關投資的書能夠讓你捧腹大笑。我讀過上百本金融書籍,只有史維德的這一本,能夠在指引、教導你的同時,也讓你狂笑。
我閱讀《客戶的遊艇在哪裡?》的次數早已數不清,就像粉絲們看著巨蟒劇團(Monty Python)的幽默短劇時跟著演員反覆念誦一樣——即使如此,我還是會對著同一個絕妙的句子發出笑聲。史維德的觀察記錄不僅趣味橫生,更是直指金錢與人性的核心實相。總而言之,關於投資這回事,除了這本你拿在手上正要開始閱讀的書,我想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趣的讀物了。祝你閱讀愉快,也希望你有所學習。
——傑森.茲威格(Jason Zweig)《錢雜誌》 (Money) 二〇〇五年九月
序 一九九五年版
我一直覺得,當我偶然發現這本有趣的小書時,作者的靈魂其實就在附近,手裡拿著一杯琴湯尼,正跌跌撞撞地走向我。當時,我正在漫無目的地翻閱著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心裡確定了一件事:若想要書寫一九八〇年代的華爾街,這裡所有關於一九二〇年代華爾街的作品,根本幫不上忙。但是,當我把最後一本滿是灰塵的書放回架上時,頓時發現旁邊還有另一本書名更耀眼、封面更有格調的書。我取下來,然後一氣呵成地讀完整本書。
早在墨基爾(Burton Malkiel)寫出《漫步華爾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之前,小弗雷德.史維德早就親身在那裡漫步了。他在大四時被普林斯頓大學退學,原因是他在某一天早上六點被抓到宿舍裡藏著一個女孩;後來他便來到華爾街工作,那是一九二〇年初的事。他只在這裡待了短短幾年,關於華爾街經驗的書,也只寫了這麼一本;但卻是精華之作。他以詼諧手法寫出了當時的華爾街,現在讀來仍然妙趣橫生。我們的年代有太多所謂「幽默」實則無趣且不知所云的作品,但這本書卻永遠能夠戳中你的笑點。我認為,這部作品能夠持續保存著生命力,原因在於其中內容在多年之後仍舊緊扣著我們今日的經驗。
史維德以深入淺出的語言,直指投資行業最精神錯亂的核心:人們普遍以為,總會有個人能夠告訴你如何用一小筆錢快速致富。如果這一切確實存在某個指引性原則的話,那就是:「挑選可獲利的投資機會,這是一份幾乎不可能勝任的工作。這樣的專業能力不存在供給來源。」但是,仍然有許多人不斷提供投資建議,而聽取這些建議的人就更多了。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們的作為呢?史維德親眼目睹著投資行業的大小事,他不僅未感到憤怒,甚至被其中的種種行徑給逗樂了。他如此寫道:「經紀人對市場的未來有一些看法,以此影響他的客戶;但他們跟客戶說的,確實是他們信以為真的事。最糟的是,他太急於說服自己相信某些事,而最後確實就輕易地以一些拙劣的想法說服了自己。」
史維德書寫的重點不在於罪惡,而是華爾街的荒唐;如此選擇,或許也跟他的性情有關。他的父親是個放空交易者,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多頭市場中破產。成年後的史維德大部分時候居住在美國康乃狄克州諾沃克市(Norwalk)郊區的羅威頓(Rowayton);他稱這個地方為「諾沃克南邊的雅典」。他愛打高爾夫球,喜歡邊工作邊喝酒;他只寫過少數幾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童書《古怪小男孩》(Wacky, the Small Boy)。一九六〇年刊登在《紐約時報》的訃告,使用的是他畫在護封上的自畫像:「體重曾達一百八十二磅;二戰前的照片都是棕色捲髮;我的一切都是母親給予的,一小部分來自於其他人;喜歡純潔無害的娛樂,前提是你能找得到純潔無害又不讓人窒息的樂子。」對於自己的著作,他必定樂在其中。
——麥克‧路易士(Michae; Lweis)(筆者為《大賣空》、《魔球》作者)一九九五年
作者前言 一九五五年多頭市場版
這本書在十五年前首次出版,當時金融市場的情況跟今天不同,作者的際遇也不盡相同。
然而,像法國人所說的: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世事變遷,有些事到頭來卻依舊如初)。時至今日,我對這句話更是深信不疑。
出版十五年後仍然被記得的書實在不多;但是,一九四〇年當時對華爾街有所關注的人當中,我知道有不少人記得這本書。其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購買或閱讀了這本書,有的甚至連書裡阿諾(Arno)先生的插畫也沒瞥上一眼。我遊走各地時,發現有許許多多的人知道這一本書,但從沒有買過。每每我在談話中提起《客戶的遊艇在哪裡?》時,大多數人的眼睛總會為之一亮。
這本書會留在人們的記憶裡,全歸功於四萬字之中的這幾個字——也就是這本書的書名。現在正是適當的時機,讓我透露寫作這本書的靈感來源:
一切源自於那則小故事(請看第三十八頁)。一九二七年我在華爾街找到第一份工作,不久後我就聽到這個笑話;所有在那裡工作的人都聽過。數十年來這則故事只是一直埋藏在我的潛意識裡;畢竟,這不是一個適合在聚會場合裡說的笑話,因為那裡的每一個人早就聽過了。於是,我在初稿裡的某處寫了這個故事。我的編輯古德曼(Jack Goodman)先生卻把這一句挑了出來,放到書背上。
我還記得我當時大力反對,但一如既往的,反對無效。我的弟弟是著作權法方面的專家,我從他那裡得知書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所以,我早就想好了要給我的書一個好書名——《頑童歷險記》。
這本書面市且進行廣告宣傳之後沒多久,我就收到許多老華爾街人的來信,他們指責我抄襲。其中一位來函者語氣相當客氣,卻為我提供了相關的資訊。這位老紳士特地為我寄來了我出生那一年在舊金山出版的《閒談者》(The Tattler)期刊影印本。其中的評論我讀得入迷,那是來自一位崔維斯(Travis)先生的碎念;這位崔維斯先生是個睿智的人,他當時的名望僅次於劇作家威爾森.麥茲納(Wilson Mizner)。我知道崔維斯先生有一點口吃,因此當他提到刮著冷風的那一天,他站在水族館旁顫慄不已時,情境更為動人。出於學術精神,這本書的書名其實應該改名為《客客客客戶的遊艇在哪裡》。
我很清楚:這個我「偷竊」而來的笑話本來就有甚高評價,否則就不會流傳半個世紀之久。這跟我的引用沒有關係。
關於這本著作,我最喜歡的一篇書評(實際上,即使納入我讀過的所有其他書評做比較,這篇仍是我的最愛)是沙利文(Frank Sullivan)所寫的。
我過去並不認識沙利文先生,但因為他的書評,我們倆通信了好一陣子。書評的部分內容如下:
「〔史維德先生〕認為華爾街人本質上是無可救藥的幻想家與小孩。我們難道不是嗎?一九三七年我以四十元買進賓州鐵路公司股票時,我也以為自己已經是個成人了——」
「——華爾街或許應該有更多如此古怪的哲學家。如果我是摩根(J.P. Morgan),我會毫不猶豫地邀請小史維德來當我的合夥人;但很顯然我不是。」
於是,我坐下來慎重地寫了一封信,由《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書評欄編者轉交給沙利文先生。
「親愛的沙利文先生:
你為我的著作寫了一篇極為出色的書評,為此我不勝感激。但是,我急於與你相談的事,與寫作無關。你的文章裡有其中一段我深感興趣。你說,如果你是摩根,你會邀請我當你的合夥人;但你隨即卻強調你不可能是摩根先生。不瞞你說,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業務不如預期。如果當上摩根的合夥人,我的事業生涯將會有另一番轉折,或至少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因此,我發現我的未來跟你的身分已經構成了緊密關聯。我懇請你再仔細檢查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偉大的金融家摩根先生,還是優秀的詼諧作家沙利文先生。當然,如果你發現自己終究沒有那一大把黑色大鬍子,那麼我們的夢想也就只能落得一個破敗不堪的境地了。如果你幫得上我,我也有個主張,作為給你的回報。在未來的任何時候,如果我發現我自己是奧格頓.雷德夫人,我會聘請你當《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總主筆,薪水由你決定。不過你的薪水要求必須合理,我想這一點你也了解的。
某某某 敬上」
我很快就收到回覆。唉,他終究是沙利文。那封信實在太讓人失望,我隨手扔了。但我到今天還記得他在信裡所說的重點。他非常有禮且真誠地希望我成為奧格頓.雷德夫人,但這對我來說太艱難。不過,他對我還有另一個比較簡單的要求¾¾如果我能夠把賓州鐵路公司的股價推回到四十元,他將永遠感念於心。
我不必費多大功夫就取得了賓州鐵路的報價,一看,價格落在十一點五至十一點二五元之間。我背脊一涼,心底冒出一句:「靠!」
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天寫下這一段文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已經幫他把股價推回到四十元了。
當我被告知今年是推出新版本的好時機時,我心底盤算的是:好的,我會把整本書再重新細讀一遍,如果有哪些內容未能通過這十五年歲月的考驗,我將一一改寫。但是,一番深思後,我決定要大膽地喊出:「一字不改!」既然已經存在這麼久,就讓這一切以原有的樣貌繼續存留於世吧——甚至連我拼錯的某家美國知名銀行的名稱,也不改正。(你想不想知道後來他們有沒有開除那位校對員?)
這個版本應該是作為一本回憶錄而存在,記錄的是十五年前我所處的情境;而在那之前,我在那片高樓聳立的園地裡辛勤工作了十五年。回憶錄不需要潤飾,過多的修改會毀壞回憶錄的價值。像我這樣的人,當然會選擇使用最坦率的方式¾¾同時也是最容易的方式!
書寫這本書的那一年,華爾街一片蕭條,股價普遍低迷,幾乎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點。股價偏低的市況不太會擾動人們的情緒,那時候的投資大眾對華爾街的興致大概就跟他們對室內網球場的興緻一樣低;只有少數有錢的古老家族會對這兩者感興趣。所以報價帶就像一條乾涸的小溪,經紀商則有大把的時間下棋,甚至寫書。
但是,過去我在這艘裝有馬達的戰艦上工作的那些年,我見過所有的事,而且大部分所見所聞都叫人為之愕然。首先,我有幸得見所謂「狂飆的二〇年代」最後那三年。然後,我突然坐在一個絕佳的席位,目睹著股市大崩盤在我面前上演——那三個月,是歷史上一段猛烈、悲慘,而且極度戲劇化的時期。不久之後,雖然萬分不情願,我還是被迫成為了經濟大蕭條的目擊者與參與者。
這遠遠比一時的市場崩盤更悲慘,那本該是惡夢裡才有的悲劇情境。那是夢境般恐怖,卻又枯燥乏味的年代。許多大人物似乎都快要撐不下去了,就像是夢魘者驚醒前的感覺一樣;跟大眾觀感不同的是,這些大人物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好人。然後,我相當讚賞的新任總統透過電台說出了有史以來最有力的八個字,於是重新打開了銀行的大門(之前關閉銀行的也是他,當然理由也很充分)。眨眼間,惡夢就過去了。
大約四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市場迎來了另一次小恐慌,但一切仍在控制範圍之內。後續的四年,華爾街沒發生什麼大事,日復一日的風平浪靜,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你要了解,我這裡所說的都是華爾街的事;華爾街以外的世界,這段時間當然發生了很多事。
我離開華爾街沒多久,我想大概是隔天吧,股價便開始上漲——而且自此一路不停地上漲,中間偶有回檔,但幅度微乎其微。我想這跟我的離開應該沒有關係。
我從來沒再回去從事那個行業,但偶爾會以客戶的身分回到華爾街。你或許以為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如今我在華爾街走動時不會有薪水可領。其實不然,真正的差異在於華爾街對待我的態度。現在,當我在早上十一點半閒逛到某個經紀商辦公室時,不會再有主管發狂似的對我咆哮,說我又拖拉又愚笨——雖然這說法對於作為客戶的我來說也是貼切的。他們那精神抖擻又恭敬有禮的態度,已近乎阿諛奉承,尤其當他們從我的舉止之中觀察到我當天有意買進某支股票五十股的時候。
本書舊版中除了一處拼錯和一些不成熟的評論之外,可能招致批評的大概就是有關投資信託的那一章——這類投資工具當時確實就叫作投資信託。我好像帶著有點居高臨下的態度在評論他們。自從那些溫和的挖苦文字變成無可抹滅的印刷品之後,這些公司的身價便節節上漲。
投資信託公司的成長,比起同時期某些個股的投機性暴漲,更為意味深長。投資信託公司如今數量龐大,當中大部分屬「開放型」的投資公司,現在被稱為「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不太可能是客戶一時心血來潮而購買的東西。基金公司有一個辛勞工作的銷售團隊,他們推銷的範圍不僅限於熟知股票投資的沿海地區與大城市居民;實際上他們不斷開拓新疆域,尋找新客源。他們主動打電話給任何人,向他們介紹自家的投資產品,並且耐心解答問題。如果對方給予正面回應,他們便會繼續撥打;如果對方給予的是負面回應,他們也會繼續撥打。他們看來就跟保險推銷員無異。你大概還記得上一次找你的那個保險業務員——他一開始有點讓人不舒服,然後變得有些討人厭;最後,他就把保單推到你眼前了。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你會深情地看著你的保單,慶幸自己是個負責任的公民,更是個愛家的男人。
十五年過去,如今我們大可以說:共同基金推銷員為那些心不甘情不願的客戶所帶來的福祉,甚至多於保險業務員所帶給他們的。無論如何,至少到目前為止確實如此。
我發現我在第一〇四頁加了一個註腳,說明「投資信託」是不適當且不精確的名稱,業者應該另取一個更好的。他們真的這麼做了,但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人為此向我道謝。還有另一件略帶諷刺意味的小事件:正當我對這個主題寫下那些挖苦的文字時,我卻意外地成為某個優良投資信託的獲利者。那是一家「封閉型」投資信託公司發行的受益證券,當時沒有業務員向我推銷,我基於個人判斷,或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透過紐約股票交易所購買。幾年之後,我竟然發現這些證券的價值已經翻倍。我覺得這實在太荒謬了,隨即透過紐約股票交易所賣給某位無名的陌生人,我想他肯定是個好運的傻瓜。賣出的決定,也是出自於我的個人判斷。我當時打著如意算盤,想要等待價格下降到更合理的水準,再買進。
後來我就沒再買進了,因為價格從此以後就一路上漲。至於漲到哪裡,我沒心情在這裡多談。針對這第二筆交易,我的評論只有一個;但我無法在日常慣用的詞彙裡找到適當的表達方式。
欸。
我想從來沒有讀者會這麼無禮地探問一個專業的財經作者:你知道這麼多關於理財的事,但為什麼你沒有變富有?然而,許多讀者必然會私下納悶。我願意嘗試為這樣的讀者解答,但我無法給予完整的答案。
以我為例,成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我不只是漫不經心地書寫財經相關的內容,也在普通股的買賣之中瞎混。優先擔保債券鮮少激起我的興趣。自從這本書出版以來,普通股市場的價格已持續上漲了十五年,目前達到自古羅馬時代以來的最高點。但我名下還沒有一輛凱迪拉克(Cadillac)轎車。
我想,如此平庸的成就跟我年輕時易受影響的個性有關。那段期間,我工作的交易台對面坐著的是個老人——他是個終日冷嘲熱諷的愛爾蘭人,而我總是默默地欣賞他那憤世嫉俗的個性。我常常聽到他喃喃低語地說著他的至理名言:「這些證券是被創造出來幹嘛的?就是為了要賣啊。所以,儘管賣掉吧。」
此後,我便傾向於買進股票,而且是盡己所能地買進;然後,一旦顯示有利可圖時,我就滿心歡喜地賣掉。(當然,我不會在六個月之內賣出。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對我而言,這種時刻帶給我的似乎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獎賞——什麼都不用做,就能賺到一些錢。很久以後我才發現,我應該在買進股票之後,就像個肥胖、懶惰的鄉下人一樣,一屁股坐在股票上面。這樣的一個鄉下人,因為懂得節制貪婪之念,最終坐擁財富。
書籍基本資料
- 分類:股票
- 作者: FRED SCHWED JR.
- 譯者: 陳民傑
- 出版社: 寰宇出版
- 出版日期:2017-10-07
- ISBN:9789869451987
- 商城書號:F414
- 規格:25開本/ 220頁/淨重約316g
加購商品
-
加$360購買定價:$480元 2017-2019投資大進擊:全球趨勢專家首次揭露一輩子一次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外匯交易精論
-
加$210購買定價:$280元 3天搞懂中國投資:搭乘「貨幣直航」,直掏13億人腰包,錢滾錢
-
加$280購買定價:$400元 散戶升級的必修課
-
加$182購買定價:$260元 點時成金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掌握台股大趨勢
-
加$266購買定價:$380元 《交易大師》操盤密碼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賺遍全球:貨幣投資全攻略
-
加$240購買定價:$320元 我如何在股市賺到200萬美元(經典紀念版)
-
加$225購買定價:$300元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窮理財法」提早
-
加$600購買定價:$800元 賈伯斯傳:Steve Jobs唯一授權 (最新增訂版)
-
加$338購買定價:$450元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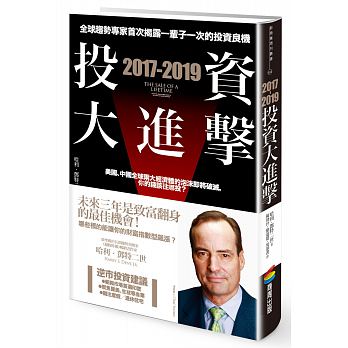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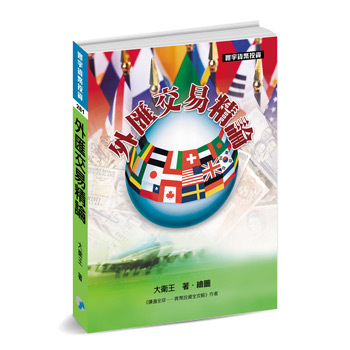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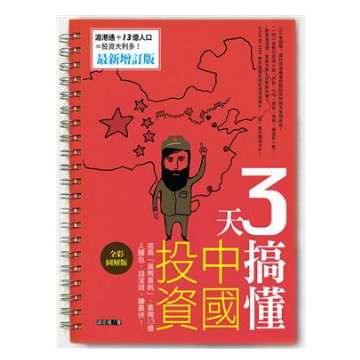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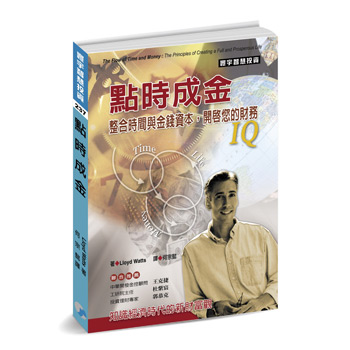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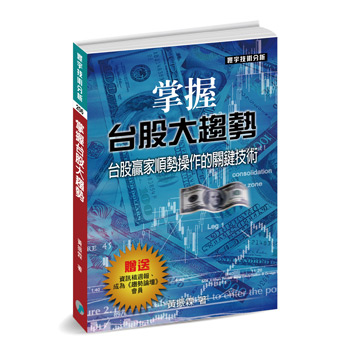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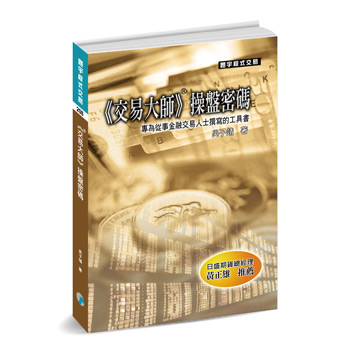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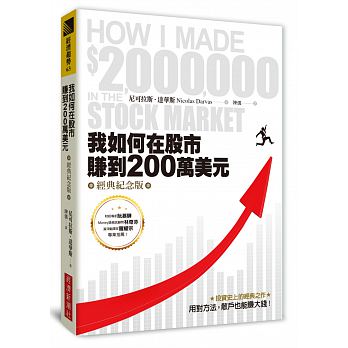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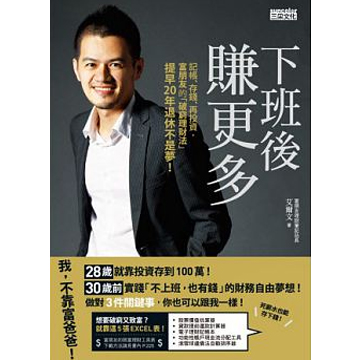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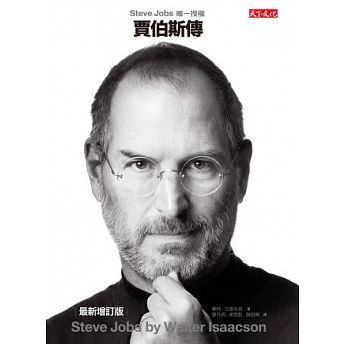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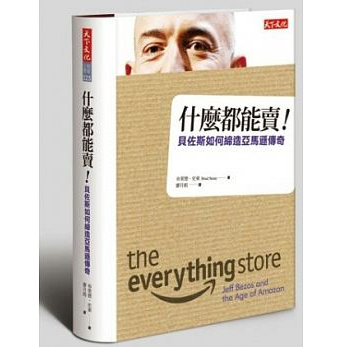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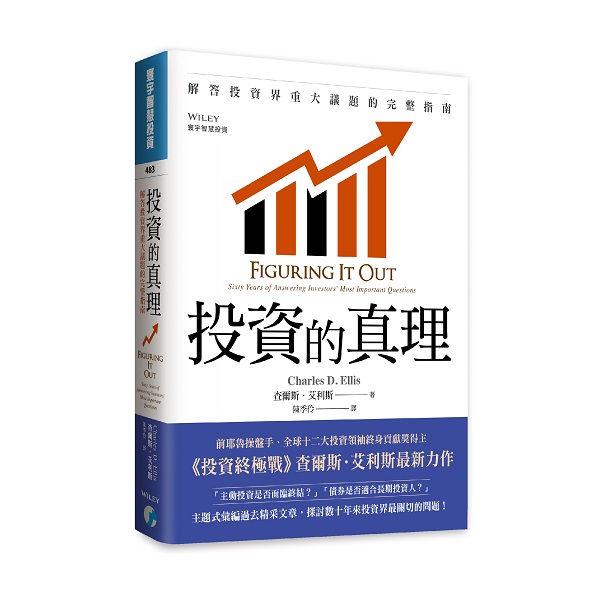



 Search
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