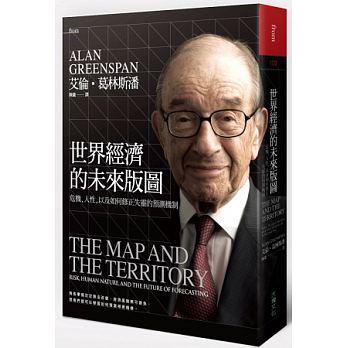
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 危機、人性, 以及如何修正失靈的預測機制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
-
定價
450元
-
優惠價
88折396元
-
會員價
79折356元
-
加贈點數
0點
- ※購書免運門檻,大宗購物流程,詳見"常見問題-財金書城相關"。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富比世》雜誌好評推薦
預測機制失靈,表示我們對人性不夠了解。
經濟未來的重要議題,本書有宏觀討論。
「或許很多人認為,葛林斯潘的成名之路不符常規,但讀過這本書之後,你會了解為何有多達五位美國總統都曾請求他的協助,使他成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政策制訂者之一。」
──葛雷葛利‧麥基(N. Gregory Mankiw),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葛林斯潘和每個人──儘管只有少數人的能見度像他那麼高──不得不對風險管理與經濟預測的某些根本假設產生懷疑,因為放眼世界各地,沒有任何一個經濟決策圈要角事先預見這場風暴。到底為什麼我們的預測模型,會讓我們這麼一敗塗地?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葛林斯潘在幾年前,展開了嚴謹且廣泛的研究。他檢視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如何預測未來的經濟情勢,並探究要如何預測得更精準。從家庭、企業到各級政府,不管在任何領域,經濟風險都是無可避免的。無論是否體察到,我們每天幾乎都會以某種方式對未來下注。然而,在下注的同時,我們卻經常被過時的認知誤導,否則就是隨著人類知覺所無法控制的要素起舞。
本書的目的,就是企盼更新我們的預測概念網。它融合了經濟預測史、行為經濟學家的新研究成果,和作者本身豐富、顯赫的職涯閱歷,提供一個清晰到令人震撼且具實證根據的基礎,讓人更加了解我們過去對經濟預測的認識還有無知。本書也探討文化是否注定無法改變,並探究我們可以從福利國的債務與改革,以及全球暖化時代的天然災害中,預測這個世界即將面臨哪些最大的潛在挑戰。
當然,任何內心的認知地圖,永遠都不可能和現實版圖完全吻合。但葛林斯潘提出的方法,是以他特有的嚴謹、智慧與空前分明的脈絡為基礎,所以這份獨特的認知地圖,絕對有助於個人、企業乃至國家,透過很多不同的道路,安全地度過未來的旅程。
專業推薦
李紀珠 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
吳中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邱正雄 永豐銀行董事長
胡勝正 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國源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綠角 財經作家
鄭貞茂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為什麼全球計量經濟模型,未能預測出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葛老以『人性』來補強計量經濟模型的不足。貌似嚴謹的計量經濟模型與看似不太科學的人性相輔相成,就燦然全備了。」──李紀珠,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
「這是一本兼重專業與通識的巨著。全書深入淺出,非葛林斯潘無此功力。相信除了金融與經濟學家、政策制訂者應讀外,一般讀者亦會因易讀此書而受益甚深。」──邱正雄,永豐銀行董事長
「葛林斯潘卸任後發生全球金融危機,頓時幾乎成為眾矢之的、聲譽掉漆,但批評者往臉上貼金的成分大於對葛氏的打臉。將本書視為葛林斯潘的職業生涯經驗精華也不為過,論點極具啟發性,有高度的參考價值。」──胡勝正,中央研究院院士
「宏觀的經濟觀點,可以讓我們看清個人投資計劃與職業生涯面臨的挑戰。想要更能掌握自己的經濟未來,你一定要了解經濟的本質。而這本書,就是一本當代經濟的深入導覽手冊。」──綠角,知名財經作家
「葛老終究是葛老,金融海嘯後這麼多年仍孜孜不倦進行研究,並提出最新觀點。面臨未來全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對所有的經濟參與者而言,應該要如何因應?相信讀完本書後,你定會激發出自己的想法。」──鄭貞茂,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本書涵蓋的主題和論述既深且廣。當前華盛頓政治圈充斥著泛政治化與狹隘思維,相形之下,葛林斯潘的格局、眼光和果敢,更顯彌足珍貴。」──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即使是一般讀者,也能理解這本書所陳述的複雜、深奧議題。所有對金融市場運作模式,或是對市場運作失靈有興趣的人,都應該拜讀這本書。」──伯頓‧墨基爾(Burton Malkiel),《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本書蘊含了深遠的智慧,葛林斯潘透過和很多專業同儕完全不同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或許很多人認為,葛林斯潘的成名之路不符常規,但讀過這本書之後,你會了解為何有多達五位美國總統都曾請求他的協助,使他成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政策制訂者之一。」──葛雷葛利‧麥基(N. Gregory Mankiw),《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是一本極具說服力、更富教化意義的書。書中充滿可供金融從業人員、證券分析師、商學院學生和公共政策制訂者,尤其是總統、國會議員、中央銀行官員等參考的獨到見解與教誨。」──《富比世》(Forbes)雜誌
Alan Greenspan 【艾倫.葛林斯潘 】
生於1926年,在紐約市附近的華盛頓高地長大。在茱莉亞(Juilliard)音樂學院修習單簧管,並成為職業演奏家後,取得紐約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54年,共同創辦了陶森葛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
1974年至1977年間,擔任福特總統旗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1987年,被雷根總統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直到2006年退休時,他都一直擔任這個職務。
著有《紐約時報》暢銷書第一名《我們的新世界》。
推薦序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葛老在本書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為什麼全球計量經濟模型,沒有任何一個能預測出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他以「人性」來補強計量經濟模型的不足。
所謂的「人性」,葛老從凱因斯的「動物本能」談起,列舉各種傾向。最後他歸納整理,認為樂觀偏誤、陶醉、羊群行為、恐懼等幾項,是造成景氣循環轉折點難以被計量經濟模型預測的人性因素。
樂觀和陶醉造成大多頭市場,羊群行為加強大多頭市場的強度(導致計量經濟模型失靈),「高處不勝寒」的恐懼感,讓市場流動性戛然凍結。經過這樣的處理,我們看到貌似嚴謹的計量經濟模型「尺有所短」,看似不太科學的人性反倒「寸有所長」,相輔相成就燦然全備了。
李紀珠
(本文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中華民國銀行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推薦序
一本深入淺出的巨著
這是一本兼重專業與通識的巨著。本書除了論述利率、股價、貨幣政策、景氣、金融風暴等重要金融、物價與經濟議題外,亦包括其他廣泛的重要闡述,如金融風險遠大於實體經濟風險、生產力、儲蓄、消費、投資與社會福利政策、全球化與所得分配不均、人口與經濟成長、政治安定與分裂、企業與文化等。
葛林斯潘挾其擔任美國聯準會十八年半主席的豐富資歷,在本書羅列豐富數據,以理性經濟人為基礎,結合現代認知心理學所強調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傾向分析,做為其嚴謹論述的基礎。全書深入淺出,非葛林斯潘無此功力。相信除了金融與經濟學家、政策制訂者應讀外,一般讀者亦會因易讀此書而受益甚深。
邱正雄
(本文作者為永豐銀行董事長、前財政部部長)
推薦序
職業生涯經驗的精華
葛林斯潘是位才子、傳奇性人物。他的音樂造詣甚深,是職業演奏家,後來改行修讀經濟學,成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在華爾街發光發熱。1973年,美國福特總統任命他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87年起,他擔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前後18年,深獲不分黨派、歷任總統的信任。
葛氏主政聯準會期間,美國經濟繁榮、穩定成長,許多人將之歸功於葛氏貨幣政策的得當。他卸任之後,發生全球金融危機,頓時幾乎成為眾矢之的、聲譽掉漆,但他的批評者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成分大於對葛氏的打臉。畢竟,在危機之前,葛氏就一再提醒大家注意「非理性繁榮」,只是他的警語被當耳邊風。在本書,他再度警告,未來相似的危機還會不斷復發,雖然無法確定其精確本質。
本書是葛氏致力後金融危機研究的心得,全書14章,聚焦為何大家都嚴重預測失準,未預見危機發生,也要探究我們學到了什麼教誨。就戰略層面而言,本書認為,美國所以面臨許多嚴重的長期經濟問題,是由於對經濟未來投資不足之故。其中最值得憂慮的是,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如果不能忍受短期的痛苦,採取果斷的補救行動,美國終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危機之後,美國國會通過陶德—法蘭克法案,大幅提升金融監理的強度。葛氏並不贊成這種做法,認為這些新規定對生產力造成傷害,如果金融監理所引起的不確定性加以消除,讓股票風險溢酬回歸到正常值,光靠股票與其他資產價格的上漲,就足以激勵近年來奄奄一息的就業市場。他強調,金融監理要注意成長與穩定的平衡,金融危機引爆的癥結在於金融機構過度槓桿,資產負債表資本項目受到損害之故,所以監理的重點在於資本適足,在於經濟資本。
危機之後,美國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大量注入流通性。葛氏在本書雖未明言反對,但他強調,只有在最極端的金融崩潰時期,才能用主權信用來支持金融體系。
與金融危機息息相關的,是美國財政失衡。葛氏特別警告,如果未能解決具破壞性的財政失衡,美國隨時可能爆發另一場金融危機。美國財政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險支出的快速上升,已嚴重排擠其他政務支出與民間儲蓄,導致民間投資與生產力下降,而未來還有龐大的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儘管社福支出快速成長,戰後所得分配不均趨勢也一路上升,導致美國政治體系出現非常大的裂痕。葛氏認為,社會安全制度應大刀闊斧加以改革,但這是政治層面的問題,誰能拿起大刀、說服選民,將是新的政治英雄。
本書雖是後危機研究,將之視為葛氏職業生涯經驗的精華也不為過。本書論點極具啟發性,有高度的參考價值。有關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的警語,如果用在台灣,相信也說中了許多人的心坎。
胡勝正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中央大學國鼎講座教授)
推薦序
掌握經濟未來,必先了解經濟本質
作者葛林斯潘先生,在本書以其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經歷,與對各國經濟的深入觀察,帶領讀者進一步了解全球經濟。全體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否有可尋的脈絡,向來是投資者與經濟學家醉心研究的課題。對投資人來說,假如能預知未來的經濟走勢,就可以先一步採行動作,避免金融資產的損失。對經濟學家來說,假如可以掌握經濟脈動,就可以以適當的政策應對,試圖避免蕭條與過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書提到過去許多預測失敗的例子,例如在二次世戰後,一般預測因為軍事支出大減,美國經濟將會進入停滯或低成長期。或是,在1970年代的高通膨環境下,一般認為美國聯準會不會採行強力緊縮措施來壓制通膨,因為這將帶來失業率大增的慘痛代價。事後發現,當時的這些共識,都不是歷史發展的軌跡。
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是近年鮮明的例子。當時一般認為,美國經濟的弱點,在於高額經常帳赤字。幾乎沒什麼人事先預知,房貸市場所帶來的衝擊。人們仍會試圖預測市場,但這些史實告訴我們,當經濟活動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人類非理性的「動物本能」成分時,持續準確的預測絕非易事。
所以,不論是銀行的資本準備,或是個人的投資計劃,應以準備面對不可知的衝擊做為應對方針,而不是以為放眼看去風平浪靜,便可積極從事高風險投資,然後在下一場危機中,被打得措手不及。
書中也提到,在全球化浪潮中,1970年開始,美國從事生產線重複性工作的勞工,逐漸被外國勞工取代。台灣也正經歷一個類似的轉型過程,低技術性、重複性的工作,逐漸轉給成本更低的外國勞工或是自動化設備。即便是白領階級,也面臨工作的不穩定。愈來愈現代的社會,卻似乎無法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穩定,反而是充滿挑戰與變數。
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追求更有效率的回報。當你買進股票時,你會希望這家公司的經理,追求最大的產出價值。當你買進一件產品時,你會希望每一塊錢,可以買到更高品質或更多功能。而更好的報酬與更高品質的要求,就是現代工作者壓力的根本來源。
因為出資者的要求,當某項作業可以找到更有效的工作者時,原先的雇員便會被替換。因為消費者的要求,當某類產品出現更好的新世代產品時,舊的生產線便會被廢除。在19世紀初汽車出現時,假如某個國家立法保障養馬場與馬車製造業者,到了今天,恐怕會變成全球運輸效率最差的國家。在智慧型手機出現時,假如某國政府立法保障舊型手機生產線,並規定新型手機銷售額的最高數量,那麼該國人民恐怕會很晚,才能享受到新產品的優勢服務。
當我們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與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時,舊產品與低效率的生產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被替換。當身為消費者的我們,要求更舒適、更好的生活時,也會對同時身為工作者的我們帶來壓力。人們無法同時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與不變的工作保證。
宏觀的經濟觀點,可以讓我們看清個人投資計劃與職業生涯面臨的挑戰。個人,無法逃脫大時代的影響。想要更能掌握自己的經濟未來,你一定要了解經濟的本質。而這本書,就是一本當代經濟的深入導覽手冊。
綠角
(本文作者為知名財經作家)
推薦序
對預測要嚴謹,對市場要謙卑
葛林斯潘曾是全球財經界最有影響力的央行總裁,卻在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中英名受損,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在2003年,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從1.25%調降至1.0%的歷史低點,有些人認為這是後來美國房市走向泡沫的遠因之一。另外,葛林斯潘也曾經讚譽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明及其他金融創新,協助美國長期利率走低,是美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金融海嘯過後,這些談話聽起來格外諷刺。
但葛老終究是葛老,即便在金融海嘯過後這麼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並提出最新觀點。葛老認為,經濟預測失靈導致政策對應不當,其中的關鍵因素,便在於對人性的研判。這也是為何政府官員及財經學者,對於金融危機雖然已有許多研究,卻仍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印證在台灣的政府政策也是一樣,儘管政府政策有許多對台灣經濟的中長期規劃,若無法說服民眾並獲得支持,那麼許多政策的美意便無法施展,反而形成政策與民意的落差。尤其是金融海嘯過後,美國政黨對立日益嚴重,葛老擔心政治體系分裂的結果,將對美國長期經濟走勢不利。這對台灣來說,無疑也是一記當頭棒喝。
身為市場派經濟學家,個人對於未來全球經濟情勢的變化,一向非常關切。但我也認知到,倘若只關注短期市場走勢,往往會忽略中長期經濟結構變化所產生的更大衝擊。而預測工作最難的地方,往往也是當經濟結構發生轉變、導致成長模式轉變時,過去的成長型態已不能再做為未來預測的參考基準,此時的預測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這使我想起當初入行時,金融前輩對我的教誨即是:「對預測要嚴謹,但對市場要謙卑。」因此,面臨未來全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對所有的經濟參與者而言,應該要如何因應?相信讀者在讀完這本書後,定會激發出自己的想法。
鄭貞茂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推薦序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李紀珠
推薦序 一本深入淺出的巨著 邱正雄
推薦序 職業生涯經驗的精華 胡勝正
推薦序 掌握經濟未來,必先了解經濟本質 綠角
推薦序 對預測要嚴謹,但對市場要謙卑 鄭貞茂
前 言 失靈的預測機制
1 動物本能
2 危機的爆發、惡化與平息
3 危機的根源
4 股價與民間權益的振興效果
5 金融與監理
6 經濟預測發展史,以及我的經濟預測之路
7 不確定性損及投資意願
8 衡量經濟成就的終極指標:生產力
9 生產力與應得權益的年代
10 文化
11 全球化、所得分配不均、裙帶資本主義的風險
12 貨幣與通貨膨脹
13 緩衝資源日益耗損
14 結論
謝 辭
附 錄
注 釋
關鍵字:大塊出版/ Alan Greenspan 【艾倫.葛林斯潘 】/ 陳儀
精彩試閱
前言 失靈的預測機制
2008年03月16日,是個寒風刺骨的週日。那天午後,我打完一場室內網球後返家,一進門,就接到一通我做夢都想不到的電話。聯邦準備制度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下文簡稱聯準會)一名資深官員打電話通知我,聯準會剛剛宣布將行使它幾十年來未曾動用過的一項法定權利──鮮為人知但威力強大的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13條第3款。廣義解讀,第13條第3款授權聯準會無限額借錢給任何一個人。在03月16日當天,聯準會隨即授權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向摩根大通(JPMorgan)融通了29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它購併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當時陷入破產邊緣的貝爾斯登成立於1923年,是所有大型投資銀行中規模最小的一家,破產事件爆發前,才短短一週,它就耗盡了近200億美元的現金。該公司破產後,全球金融陷入動盪達六個月之久,而這一波動盪在2008年0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時達到最高潮。雷曼兄弟的倒閉,引爆了堪稱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機。當然,在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經濟活動崩潰的程度遠比這次金融危機期間更嚴重,但在歷史上,扮演日常商業活動主要促進力量的短期金融市場,卻從未出現這次的慘況,幾乎全面關門大吉。隨著投資人的心情從極度陶醉轉為極端恐懼,平日流動性最高的幾個市場,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枯竭,金融環境頓時變得異常詭譎複雜,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也因此大幅萎縮。在那個攸關重大的九月天,以及接下來的幾週裡,人性對經濟事務的影響,一覽無遺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表面上看來,這場金融危機也代表著經濟預測工作存廢與否的危機。從那時開始,我便致力於後危機研究,希望能找出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所有人都嚴重預測失準,也希望探究我們從這些既定的殘酷事實裡學到了什麼教誨,而這本書就是我這段時間的研究心得。因此,就最基本的層次來說,這其實是一本和人性預測有關的書,它探討我們自認對未來有什麼了解,以及我們決定要怎麼因應那樣一個未來等。這本書不僅涵蓋了短期和長期的觀點,最重要的是,它探討了這個轉型關鍵期裡,種種令人摸不著邊際的情境。
值此時刻,我們面臨了非常多嚴重的長期經濟問題;就某種程度來說,這些問題都和我們對「經濟未來」的投資不足有一點關係。我認為,最值得憂慮的是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的問題,因為這個體系是我們賴以管理憲法相關法律規定的支柱(見第14章)。我真心期許,我透過本書提出的某些個人研究心得,能促使相關人士立即「起而行」。儘管果斷的行動,不可避免地將帶來短期的痛苦,卻有助於創造長期的集體利己效益。若不立即採取補救行動,換來的將是更難以預料的深刻苦痛,我們終將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是刻不容緩,絕對不可延宕的任務。
預測的必要性
儘管人類總是希望能夠精準預測未來,但說穿了,經濟預測從頭到尾都只是一門機率學。所謂硬科學(hard sciences)能夠準確驗明自然界的各種物理,但在經濟領域,我們似乎永遠也無法達到那樣的準確性。不過,儘管預測失敗的經驗層出不窮,預測這件事卻絕對不可偏廢,因為預測是一種天生的人性需要。畢竟,愈能預見生活環境中各種事件的後續發展軌跡,我們就愈能事先做好準備,善加回應那些事件,而這全是為了改善未來的生活。
人類經過內省而自知沒有足夠能力預見長遠未來的發展,因此,自有史書記載以來,我們似乎也基於這個自我體悟,不斷尋找各種方法來彌補這種令人扼腕的人類「缺陷」。例如,在古希臘時代,一國之君和部隊將軍會在冒險發動政治或軍事行動以前,先尋求德爾菲神諭(the oracle of Delphi)的建議。兩千年後的歐洲,也深受諾斯特拉達姆斯(Nostradamus)的神祕預言吸引。如今,世界各地還是有很多自認擁有超凡預測能力的算命師,或是偏好自己選股的投資人,他們的日子也過得還算差強人意。換言之,即使人類反覆不斷地預測失敗,卻還是阻止不了一般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設法追求預知未來的能力,因為人類的本性需要它。
計量經濟學
過去80年,模型化經濟預測學的發展,可說是人類自古追求「預知未來」路途上一個重要的關鍵期。這門學科採納了自然科學領域也使用的很多數學工具,幾乎所有官方和民間部門的經濟預測家都會使用這些工具,目的多半是為了建構足以「解釋」過去種種現象的模型,期許能藉由這些模型的建立,讓未來變得更容易理解一些。
1950年代初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修習研究所課程時期,也深受當時極為新潮的精密數理經濟學所吸引。我的指導教授傑柯伯‧沃佛維茲(Jacob Wolfowitz)和亞伯拉罕‧瓦德(Abraham Wald),恰巧是數理統計學的先驅。不過,我事後漸漸察覺到,很多看似無法模型化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狀態,會對現實世界的經濟結果,產生至為關鍵的影響。在這個認知的影響下,我對數理經濟學的實質意義開始產生懷疑,對這門學問的迷戀也因此漸漸降溫。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1936年的劃時代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為現代多數的總體經濟造模作業(macromodeling)奠定了一個基礎架構。後來所謂的「凱因斯模型」(Keynesian model),迄今仍被很多國家的政府,用來做為制訂總體經濟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然而,儘管「凱因斯模型」完整詮釋了市場經濟幾個重要單元彼此結合的模式,但無論怎麼說,它終究是個簡化版的市場經濟模型。儘管如此,各國官方及民間部門,迄今仍舊廣泛使用著一般所謂「凱因斯模型」的那類經濟模型,尤其是在探討各種政府政策對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就業水準的影響時。
凱因斯學派的觀點,等於是正面挑戰古典經濟學家的根本信念。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市場經濟向來都具備一種自我調整的能力,所以每當經濟體系遭到干擾,都會在相對短期內回歸完全就業的狀態。相反地,凱因斯卻主張,在某些情境下,那類自我平衡的機制會失去正常運作功能,最後發展為一種「未充分就業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凱因斯並倡議,一旦遭遇那樣的情境,就必須以政府赤字支出來填補整體需求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過了75年以上的時間,現代經濟學家還是為了那個政策的優點與缺失,而不斷脣槍舌戰。
無論是凱因斯學派,或是其他各式各樣的經濟預測,向來都得應付永無止境的質疑和反對意見。因為就本質來說,不管是誰提出的模型,全都大幅簡化了極為複雜的經濟現實。事實上,整體GDP的創造,有賴日常生活中數千萬、甚至上億種關係的互動,即使是相對單純的市場經濟體也不例外。而由於每一個模型,都只能呈現極小部分的經濟互動關係,其預測成效當然也就不夠理想。也因如此,經濟學家迄今仍在苦心尋覓,企盼能找出一組足以涵蓋現代經濟體系各種基本驅動力量的公式。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少數幾個簡單的公式,來掌握複雜的經濟動態。
實務上來說,模型建造者(包括我自己)在建構模型時,都會不斷修改自己選擇的變數和公式清單,直到這些模型最後推演出來的結果,看起來和歷史上的經濟紀錄相符為止。每個預測人員,都必須根據自己的經驗與信念,研判哪些「公式」最能有效掌握經濟整體動態的精髓。
大致上來說,市場經濟體系非金融產業的造模結果,都還算差強人意。因為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讓我們得以更加了解這些市場功能的運作模式。然而,誠如我們一直以來反覆受到的震撼教育,金融產業的運作環境和經濟體系的其他產業截然不同,這是一個使用槓桿的環境,涉及的風險遠比經濟體系的其他部門高。追根究柢,幾乎所有金融決策都起源於承擔風險和趨避風險的需要。相對地,非金融事業的決策,則是比較工程、技術及管理組織導向。
非金融企業當然也很重視資本投資及其他決策的風險,只不過它們的主要考量,還是聚焦在諸如「能把幾個電晶體壓縮到一個微晶片」,以及「如何確保橋晶片(bridge)能承受預設的安全運載量」等問題上。這是量子力學和工程設計的應用,在這些領域,決策雖然不是完全、但也多半與風險無關。組合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和其他新型態金融部門活動的風險程度,比起支持非金融事業領域的關鍵知識主體──自然科學領域的風險要高上好幾倍。畢竟,人類本性不可能會影響次原子粒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但人類的恐懼、陶醉、羊群行為和文化等傾向,卻會對金融活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由於金融活動能將一國的儲蓄,引導至創新技術的投資活動,所以它確實攸關重大,對經濟結果的正負面影響,也遠比表面上看到的數據──金融業的GDP占比不到10%──大很多。此外,事實證明,金融失衡無疑是造就現代景氣循環的主要直接或間接導因。總之,金融向來是經濟體系中,最難以造模的一個要素。
1960年代,甘迺迪(John Kennedy)總統和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領導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在預測模型方面的顯赫成就,讓後來所謂的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得以從學術殿堂,風光地跨進經濟決策的中心,甚至躍居最前線。到了1960年代末期,計量經濟學模型已成為政府及民間制訂決策時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這個情況迄今都未見改變。
不過,對預測家來說,經濟預測這條道路並非從此一帆風順,一路上依舊跌跌撞撞。簡單模型在課堂上充當教材還算差強人意,但很遺憾地,這些模型一旦走出教室應用到現實世界後,相關成效卻明顯未能盡如人意。就在凱因斯的典範廣獲經濟學專業領域接受後不久,美國經濟的實際表現,卻開始和所謂凱因斯模型的某些核心信條彼此矛盾。其中,凱因斯學派的一個核心信念主張,失業率上升將導致經濟體系變得更加蕭條,進而使得通貨膨脹率降低。但在1970年代的多數時間,美國經濟卻出現失業率上升,但通貨膨脹率也居高不下的景象,當時一般人將這個病徵,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到這時,此前十年間讓政府經濟學家儼然變成「先知」的預測工具,頓時變得好像漏洞百出。同一時期,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因對經濟政策的獨到見解,而獲得知識分子的青睞。他主張,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會促使通貨膨脹上升的政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張貨幣供給的快速擴張,將導致通貨膨脹預期心理上升,這種預期心理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強過隨著勞動市場蕭條而來的反通貨膨脹(disinflationary)力量。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發展了一個稱為「貨幣學派」(monetarism)的理論,和一項以貨幣供給額成長為基礎的預測工具。有一段時間,這些理論和工具對1970年代末期各種發展的預測,似乎真的比各種從凱因斯模型衍生出來的理論預測成果更加精準。到了1970年代末期,聯準會每週發布的貨幣供給數據引人注目的程度,已經不亞於今日的失業數據。
1980年代時,由於通貨膨脹獲得控制──這局部要歸功於聯準會積極壓抑貨幣供給成長,年輕化且經過適度修正的凱因斯學派再次崛起;他們修正了停滯性通膨要素,以反映通貨膨脹預期心理的重要性。接下來20年間,這些模型的預測成效都還算良好,但那多半是因為市場上未曾出現過嚴重的結構性崩壞。另一方面,聯準會的職員結合凱因斯學派、貨幣學派和其他更現代經濟理論的種種要素而建構的模型,似乎更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我執掌聯準會主席期間,這個模型對聯準會官員助益甚多。
但是,這個世界變了
儘管如此,全世界卻還是幾乎沒人預見到2008年09月的那場危機。讓經濟學專家最扼腕的是,就在我們最需要總體經濟模型的時刻,它卻明顯失靈。直到危機來襲,連聯準會那麼精密的預測系統,都未能預見到經濟會陷入衰退。即便崇高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所開發的模型,到2007年春天都還預測「自2006年09月以來……全球經濟風險(已經)降低……美國整體經濟可望維持繁榮……(而且)所有跡象都令人鼓舞。」而堪稱美國最具領導地位的金融機構──摩根大通,也在危機爆發前三天的2008年09月12日預估,到2009年上半年為止,美國GDP成長率將持續增加。
當時,多數官方和民間部門的分析師和預測人員,也都一致認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6年12月所表達的觀點:「驅動世界多數經濟體的引擎──市場資本主義(market capitalism),似乎仍舊成效卓越。」就在金融體系崩潰前一天的2008年09月14日,眾人還是高度懷疑經濟有陷入衰退的可能。那天,我參加美國廣播公司(ABC)週日早上的《一週回顧》(This Week)節目錄影,現場還有人問我:「逃脫衰退的機率,是否超過50%?」危機明明已經近在咫尺──在短短不到24小時後爆發,但一般觀點卻還是認為經濟不可能陷入典型的衰退,更遑論陷入80年來最嚴厲的經濟危機。
此外,即使在金融體系已然崩潰後的2009年01月,總統任命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還預測當時約7.8%的失業率,將在2010年年底降為7.0%,並進一步在2011年年底降到6.5%。而實際上,2011年12月的失業率高達8.5%。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哪個環節出了錯?為什麼幾乎每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訂者,都在這麼攸關重大的議題上嚴重失了準頭?
為了釐清這些疑問,我開始研究凱因斯所謂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他對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衝動,不是量化利益乘以量化機率後的加權平均(理性)結果。」凱因斯的原意,是指驅動經濟活動的各種本能,但如今我們修正了他對動物本能的定義,將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因恐懼而產生的風險趨避傾向──納入。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這種「本能」,以及相關的光怪陸離現象。
1959年,還是個毛頭經濟學家的我,犯下了此生第一個公開且令人難忘的預測錯誤。我在《財星》(Fortune)雜誌中,表示我對投資人「過度繁榮」(over-exuberance)的現象感到憂慮,但事後證明,那個大多頭市場的頂點過了很久以後才出現。重點並非我和其他經濟預測家不了解市場總傾向於表現失控,甚至會出現在任何理性基礎下不可能出現的狂亂情緒波動。真正的重點是,那樣的「不理性」行為非常難以衡量,而且任何可靠的系統化分析,也難以釐清這樣的行為。
如今,花了幾年時間深入研究人類在幾次嚴重危機期間的動物本能表現後,我終於歸納出一個看法:人類的不理性行為模式和某種系統化的要素有關,尤其是在面臨極端的經濟壓力時,而這與我原本的想法大不相同。換句話說,這種行為是可以衡量的,而且我們甚至可以將它變成經濟預測流程,以及經濟政策制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個人觀點的改變,讓最近的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本能」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所展現出來的「一致性」,將讓我們更有能力辨識股票、原物料商品和匯率等醞釀中的資產泡沫,甚至能因此預見到這些泡沫最終崩潰與復原後,會造成什麼樣的經濟後果。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尤其會試著區隔某些特定的行為需求,諸如陶醉、恐懼、恐慌、樂觀偏誤等本能差異,並探討這些本能及它們所孕育出來的文化,如何與理性經濟行為互動,進而促成各種重要的市場結果。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揚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儘管有非常多證據,證明市場行為總是很不理性,但數據也顯示就長期來說,自由經濟體依舊仰賴理性經濟判斷來指引未來的方向。當然,大家都知道,所謂的長期,有可能「非常」長。
然而,在追究2008年危機的導因,以及為何後續這幾年經濟景氣僅維持溫吞復甦、無法強勁回升的根本原因時,還是必須同時從長期及短期兩個觀點來考慮。資料顯示,1994年至2008年間,兩次資產泡沫的興起和破滅,確實對生產力的實質改善,產生一些局部的助益。不過,這些泡沫終究是一波非理性繁榮和不切實際的陶醉感所造成,總有一天,這種非理性繁榮和不切實際的陶醉感肯定會崩潰。一旦那天來臨,就會製造一種壓倒性的恐懼感,讓市場失去運作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泡沫的崩潰,都會造成2008年那麼嚴重的災難。誠如我將在第二章詳細說明的,1987年和2000年崩盤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相對來說並不大。要判斷泡沫破滅所造成的破壞有多嚴重,並不是判斷哪種資產變「有毒」(toxic),而是要判斷這些有毒資產的持有人,使用了多大程度的槓桿。這會決定感染的程度是否失控;總之,債務槓桿是最重要的,我們會在第二章進一步詳談。
書籍基本資料
- 分類:基金外匯總經投資
- 作者: Alan Greenspan
- 譯者: 陳儀
- 出版社: 大塊出版
- 出版日期:2014-06-25
- ISBN:9789862135372
- 商城書號:Q005
- 規格:384頁/精裝/630公克
加購商品
-
加$360購買定價:$480元 2017-2019投資大進擊:全球趨勢專家首次揭露一輩子一次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外匯交易精論
-
加$210購買定價:$280元 3天搞懂中國投資:搭乘「貨幣直航」,直掏13億人腰包,錢滾錢
-
加$280購買定價:$400元 散戶升級的必修課
-
加$182購買定價:$260元 點時成金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掌握台股大趨勢
-
加$266購買定價:$380元 《交易大師》操盤密碼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賺遍全球:貨幣投資全攻略
-
加$240購買定價:$320元 我如何在股市賺到200萬美元(經典紀念版)
-
加$225購買定價:$300元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窮理財法」提早
-
加$600購買定價:$800元 賈伯斯傳:Steve Jobs唯一授權 (最新增訂版)
-
加$338購買定價:$450元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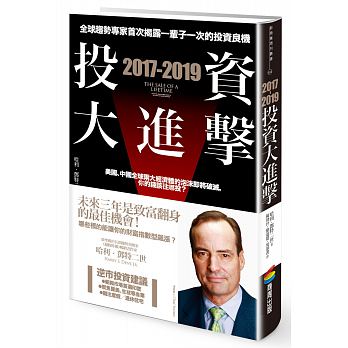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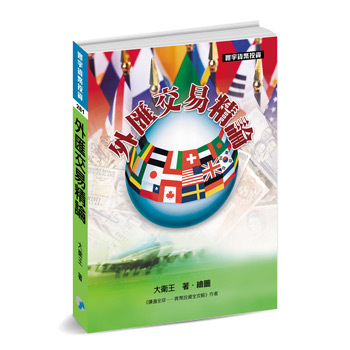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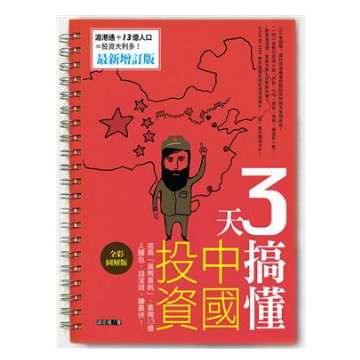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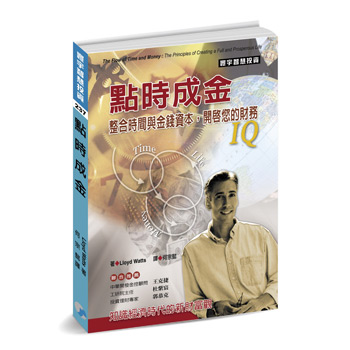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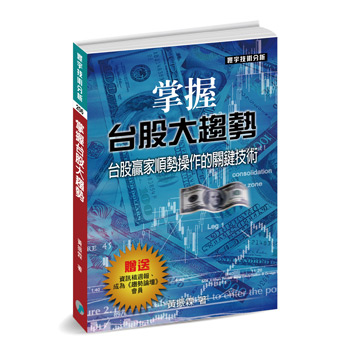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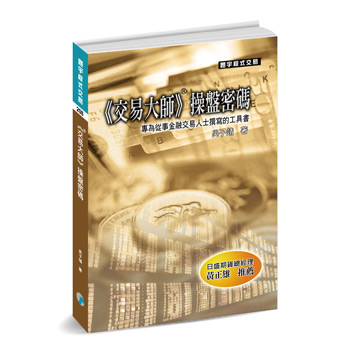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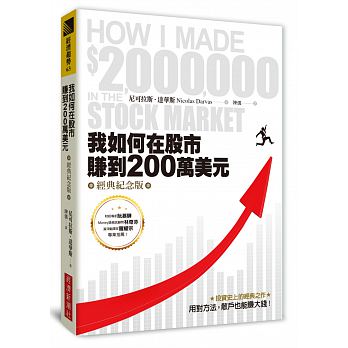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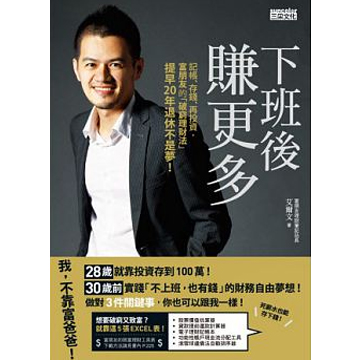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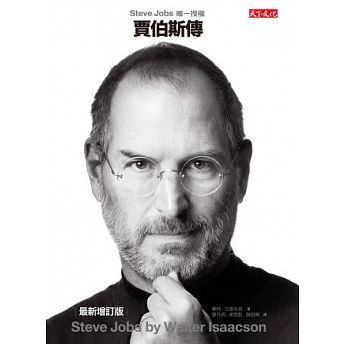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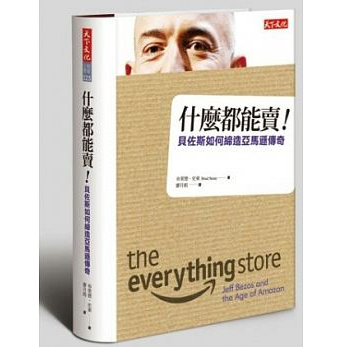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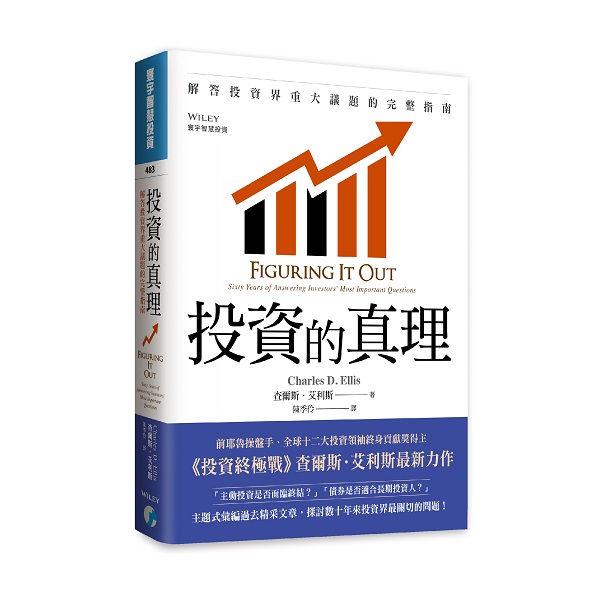



 Search
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