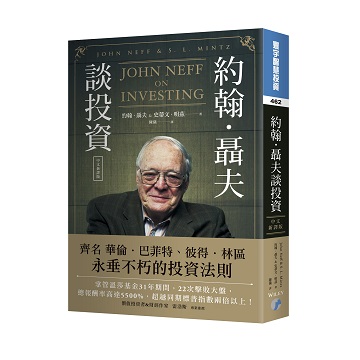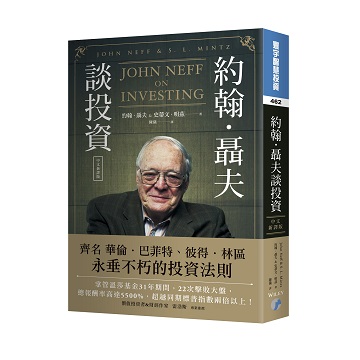約翰‧聶夫掌管溫莎基金31年期間,22次擊敗大盤,
總報酬率高達5500%,超越同期標普指數兩倍以上!
齊名華倫.巴菲特、彼得.林區
永垂不朽的投資法則
《價值投資者&財經作家 雷浩斯 專業推薦》
指數型基金教父約翰.柏格:
「溫莎的成功靠的不是過人的天資,也不是因為承擔過高的風險,
而是仰賴對證券分析與投資基本面的那分執著與專注。」
完整揭露華爾街投資大師,長期備受讚譽的投資策略
《約翰‧聶夫談投資》是一本無論投資人、經紀商、交易者或銀行家都必讀的書籍。
約翰‧聶夫終生都是個逆勢操作者,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他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逆勢而為可以帶來豐厚的報酬。在他作為基金經理人的輝煌職業生涯中,他無視一般人追捧的大型成長股,轉而選擇價格低廉、表現不佳的股票——最終也證明了他獨具慧眼。在擔任先鋒的溫莎基金和雙子星雙基金的投資組合經理的三十一年中,他於不同的市場週期下擊敗了大盤二十二次,同時將初始股份增加了五十五倍。當溫莎基金於1985年停止對新投資者開放時,它已經是美國最大的共同基金。
從共同基金管理部門功成身退的約翰‧聶夫,不吝分享讓他享譽國際的「投資者中的投資者」策略,這個投資策略也讓他得以妥善管理其他基金經理人的基金。本書首次闡述了他如何成功地運用低本益比法則,擬定相關策略、技術及投資決策,並藉此獲得了與其他當代投資大師如華倫.巴菲特和彼得.林區相提並論的成就。
本書專為那些想參考約翰‧聶夫個人化價值投資法的投資人,提供可靠的建議和指引。他長期關注被低估的股票,提出一套本益比法則作為評價標準,並藉由判讀歷年盈餘來預測新的市場週期。透過書中描述約翰‧聶夫早期生涯的〈我的溫莎之路〉,了解塑造他投資哲學背後非凡的心態和謙卑的態度。特別收錄的〈投資日記〉,則忠實地記錄他三十年來的華爾街生涯,讓讀者一窺約翰‧聶夫歷年來投資風格的演變。
John Neff 【約翰˙聶夫】
John Neff
威靈頓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的資深副總裁及經營合夥人,1995年退休。威靈頓管理公司是溫莎基金(Windsor Fund)的投資顧問公司。
Steven L. Mintz 【Steven L. Mintz】
Steven L. Mintz
CFO雜誌紐約辦事處主任。CFO雜誌是經濟學人集團(Economist Group)發行的出版品,專門探討最新的金融思潮,以及如何在今天的市場中付諸實踐。著有Beyond Wall Street和Five Eminent Contrari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