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壓力測試:金融危機的反思
Stress Test: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
定價
600元
-
優惠價
88折528元
-
會員價
77折462元
-
加贈點數
0點
- ※購書免運門檻,大宗購物流程,詳見"常見問題-財金書城相關"。
巴菲特:「本書是了解金融恐慌成因和採取應對措施的權威之作。」
面對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美國新任財長挺身而出,
親臨火線拆彈的第一手紀實!
股神巴菲特、比爾.蓋茲、《大賣空》麥可.路易士一致好評推薦
一個不被金融界看好的防火牆行動,
如何通過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的認證,
最終成為拯救華爾街的標竿?
《壓力測試》是一本關於新任財長提摩西.蓋特納在金融危機中學習的故事。
他過去曾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然後成為歐巴馬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幫助美國應對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從繁榮到衰退,從救援到復甦。在這本坦誠、引人入勝且具有歷史啟示作用的回憶錄中,他帶領讀者走進金融危機的幕後,解釋了為修復破碎的金融體系、防止大眾經濟崩潰所做出的一系列艱難選擇和政治上難以接受的決定。這是一個關於一小群政策制定者的故事,他們在極度不確定性、賭注高昂的情況下,避免了第二次經濟大蕭條的發生,然而卻在危機處理過程中遭受人民的質疑。《壓力測試》同時也是一個極具價值的政策制訂者指南,告訴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金融危機,因為這將不會是最後一次。
《壓力測試》也向公眾介紹了蓋特納部長從未嶄露的另一面。海外成長的背景,塑造了他有別於一般美國人的遼闊視野,另外,他回顧自己早年作為一名年輕的財政部官員時,幫助應對九○年代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然後描述了在華爾街繁榮時期結束之前,他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所見所聞與經歷。他將讀者帶進了危機爆發、加劇和失控的場景,討論了他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財政部任職期間最具爭議的事件,包括拯救貝爾斯登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的悲慘週末、營救美國國際集團的嚴峻考驗,以及對該公司豐厚獎金制度的眾怒。此外,他還談到了歐巴馬政府內部針對他廣受批評,但最終成功的危機處理計劃的爭議,以及為實現七十多年來最全面的金融改革而進行的激烈戰鬥。蓋特納部長還描述了危機後的餘波,包括政府努力解決高失業率、一系列關於赤字和債務的殘酷政治鬥爭,以及歐洲反覆接近經濟深淵的戲劇。
《壓力測試》最終呈現的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公共服務故事。在這本啟示性的回憶錄中,提摩西.蓋特納向讀者闡述了美國政治和金融系統所經歷的極限壓力測試過程,以及為這個人類史上最大金融危機事件的始末,留下一個最詳實的紀錄。
【各界好評】
《金融時報》年度最佳書籍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暢銷書籍
二○一四年《金融時報》最佳書籍
「《壓力測試》是前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的新回憶錄。有趣的是,蓋特納在任職期間常被指責溝通能力差,然而他所寫的這本書卻讓人欲罷不能。我已經讀過四到五本關於大衰退書籍的初稿,而我認為《壓力測試》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本,對於瞭解這段歷史有很大的貢獻。」——比爾.蓋茲(Bill Gates)
「真是令人驚嘆! 提摩西.蓋特納的書將永遠是關於金融恐慌成因和發生時必須採取的應對措施的權威之作。」——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雖然提摩西.蓋特納還有許多事情存在許多爭議,但在這裡我們要先說明,他真的寫了一本好書。在蓋特納的故事中,幾乎沒有一刻會讓讀者覺得他不夠坦率。對於一個在公共生活中花費大量時間捍衛自己,免受不負責任和不誠實的人身攻擊的人來說,這是一項超越人類極限的成就。蓋特納所做出的決定很容易受到批評,但要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並不容易。我懷疑有多少讀者會在讀完這本書後,還認為蓋特納做得不夠好。儘管他可能在演講時結巴或猶豫不決,但這卻是他非常勇敢的表現。」——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一位前財政部長毫不留情的內幕回顧,深入剖析了金融危機中令人痛心的決策和艱難取捨。這些決策摧毀了經濟,但避免了深刻且長久的蕭條。」——《時代雜誌》(TIME.com)
「這是一本貼近金融危機又扣人心弦的親身經歷,以真實感受表達了危機期間的脆弱局面,許多第一線應對人員當時驚恐的感受,以及避免大蕭條的偉大成就。這本書將以最接近的視角來看待危機,讓讀者能夠更加深刻地體驗到當時的情況,並且讓複雜的經濟學理論變得通俗易懂,讓一般讀者也能夠理解當時國家所面臨的局勢,並深刻體會到其中的驚心動魄。在此過程中,蓋特納也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的自畫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對於任何面臨金融危機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本實用的應對危機指南。蓋特納先生以他的直率著稱,而作為作者,他也沒有讓讀者失望。」——《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直言不諱、坦率無比的回憶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在整本《壓力測試》中,讀者可以深刻體會到蓋特納和他的同事們在二○○七年至二○一二年間所做出的令人緊張的決策。他有力地證明了在危機時期需要使用強而有力的手段,而聯邦儲備系統和兩任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防止了普通美國人遭受更多的痛苦。」——《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com)
股票投資、金融危機、經濟
Timothy F. Geithner 【提摩西.弗朗茲.蓋特納】
第75任美國財政部長、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
2009-2013年,蓋特納擔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領導下的第75任美國財政部長。2003-2009年總統克林頓執政時期,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卸任部長後,2014年起於紐約私募股權公司Warburg Pincus擔任總裁兼董事總經理。
作為紐約聯儲主席和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政府從2007-08年金融危機和大衰退復甦的努力中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在紐聯儲的崗位上,蓋特納協助處理了涉及貝爾斯登、雷曼兄弟和美國國際集團的危機;作為財政部長,他根據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監督了三千五百億美元的分配,該計劃是上屆政府為應對次貸危機而制定的。蓋特納同時還負責管理政府重組國家金融體系監管的工作,試圖刺激抵押貸款市場和汽車行業的復甦,要求保護主義、稅制改革,以及與外國政府就全球金融問題進行談判。
卸下部長職位後,蓋特納擔任國際救援委員會董事會的聯席主席,並在耶魯大學管理學院任教。他以外交關係協會傑出研究員的身份,撰寫了《壓力測試:對金融危機的反思》的個人回憶錄,為史上最大金融危機事件的始末,留下一個最詳實的紀錄。
簡介 炸彈
第一章 一位旅居海外的美國人
第二章 危機中的教育
第三章 逆風而行
第四章 讓它燃燒吧
第五章 墜落
第六章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七章 進入火海
第八章 有計劃勝於無計劃
第九章 變得更好,感覺更糟
第十章 為改革而戰
第十一章 餘震
後記 金融危機的反思
向危機處理團隊致敬
致謝
作者說明
附註
精彩試閱
簡介
炸彈
二○○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是我擔任財政部長的第一天,早上我在總統辦公室見了巴拉克.歐巴馬總統。自從經濟大蕭條開始發生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仍在肆虐中,他想用最快的速度永遠撲滅掉這場大火。銀行體系崩潰了,整體經濟還在迅速萎縮當中,消費者信心跌到了歷史低點,數百萬計的美國人面臨失去工作、積蓄、甚至是家園的危險。總統在白宮待了一個星期後,儘管他得到了所有的壞消息,但他看起來很平靜,還算自在。
不過,我準備再給他一些消息。
首先,我感謝他在前一天晚上來參加我的就職宣誓典禮,這是對我個人信任一種很好的表達方式。其實我們三個月前才見過面。就許多方面來說,我都不是領導財政部的正統人選,我不是銀行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甚至不是民主黨人,我是一個已經註冊的獨立人士。我沒什麼公眾形象,而且我給人的感覺也不是歐巴馬式希望和變革的樣子。過去一年,在我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行長期間,我和共和黨的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簡稱聯準會) 主席班.柏南克(Ben Bernanke),以及共和黨的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 Jr.) 一起合作設計了一系列龐大但不受歡迎的金融公司救援措施。當年我四十七歲,缺乏白髮蒼蒼的威嚴感,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個財政部長。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 是我在國會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他說,我在公開場合發言時,看起來就像是在舉辦自己的成人禮。
當時,我是政治上的瑕疵品。在確認聽證會上,我一直被描述成逃稅者、華爾街的工具、普羅大眾(Main Street) 的敵人。儘管過去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公共服務部門工作,但還是經常被人描述成一個貪婪的投資銀行家。有人認為,我可能會是自南北戰爭以來第一個被拒絕的財政部長提名人,我曾因此大受影響,考慮在投票前退出這項提名,但最後,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微弱的優勢確定擔任財務部長。然而,我對家人們被強加在身上的羞辱,以及總統不得不花在我身上的政治資本,感到極度內疚。
是開始工作的時候了。我坐在一張背對著白宮玫瑰園的沙發上,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我會坐上這張沙發數百次。總統坐在我右邊的辦公椅上。坐在我對面沙發的是著名的經濟學家,賴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他是前財政部長,他在我作為財政部門初級公務員時見過我,還幫助我晉升。現在賴瑞掌管著總統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未來我們將一起對抗危機。對我來說,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激勵人心的時刻;一個進入權力中心的職業技術官員,與一位才華橫溢的前老闆,以及鼓舞人心的新總統並肩作戰。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興奮,只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心生畏懼。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應對墨西哥、泰國、印尼、韓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金融危機。但這次是一場百年風暴,柏南克、鮑爾森和我,為各個金融巨頭設計了一系列的緊急干預措施,最後完成並產生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是一項針對金融體系高達七千億美元的干預措施,但危機並沒有就此打住,衡量企業違約風險的指數,甚至比二○○八年九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投資銀行倒閉時的指數還要高。當時股市崩盤,債券市場陷入混亂,甚至連應該是最安全的貨幣市場基金也不堪負荷,法拍屋數量也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在總體經濟方面,每月減少了七十五萬個工作崗位。
我們已經減緩了雷曼兄弟倒閉後的恐慌,但金融體系仍然處於凍結狀態。在繁榮時期過度擴張的銀行,現在正在做防禦性的撤退,他們囤積現金,剝奪企業的財務氧氣,對於想要購買新車或接受大學教育的一般借款人來說,也幾乎沒有私人信貸可以使用,更不用說想購置新房了。隨著金融地震開始在更廣泛的經濟當中產生漣漪,我們逐漸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由於被資遣的工人和其他緊張的消費者開始減少支出,企業解雇了更多的工人,也減少了投資,使得更多的家庭和企業又更進一步削減支出。癱瘓的金融體系使經濟衰退變得更糟糕,而不斷加深的經濟衰退又使金融體系更加惡化,華爾街和一般普羅大眾,一同走向衰退。我最近開始閱讀
利雅卡特.艾哈邁德(Liaquat Ahamed) 的《金融之王》(Lords of Finance),這是一部關於政策制定者的歷史;他們的錯誤,導致了經濟大衰退,也延長了經濟大蕭條的時間,不過讀了幾章後,我就不敢再往下看了,因為實在是太可怕了。
總統知道,如果不修復金融體系,他就無法解決更廣泛的經濟問題。銀行就像經濟體系中的循環系統,與電力網路一樣,對日常運作至關重要。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來保障個人的存款,讓資金可以移轉到需要的地方,協助家庭和企業投資於他們的未來,那麼,所有的經濟體系都將無法增長。然而我們的金融體系現在仍然陷在困境裡。
第四章
讓它燃燒吧
中央銀行作為繁榮的剎車器,應該在派對開始前就拿走酒杯。但是,當空氣中瀰漫著恐慌、流動性開始蒸發時,中央銀行就應該變成加速器。
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中央銀行聖經《倫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書中解釋說,阻止擠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錢放在你的窗口,告訴全世界沒有必要進行擠兌,「自由、大膽地放款,讓公眾覺得你打算繼續放款。」但這些貸款應該是昂貴的,白芝浩建議收取「懲罰性利率」,這樣一旦恐慌平息,從經濟上來說,就沒有吸引力再向中央銀行借款了,而且就像任何中央銀行的貸款一樣,它們應該有可靠的抵押品當作擔保,目標是在私人市場凍結時,能提供有償債能力的機構流動性,以保持金融體系正常運作。歐洲中央銀行在二○○七年八月九日就是這樣做的,當時,債權人被巨額的美國房屋抵押貸款曝險部位給嚇壞了,紛紛從歐洲銀行撤出資金,許多銀行正在喪失流動性,但歐洲中央銀行告訴他們:我們有現金,如果你需要它,隨時來拿。
柏南克主席相信白芝浩,他相信在危機中,如果中央銀行不採取行動,就可能會使危機進一步惡化。柏南克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直是研究大蕭條的主要學者。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表明,一九三○年代的中央銀行太過膽小,太不願意提供流動性,太忠於當時緊縮貨幣的正統理念,導致銀行倒閉和信貸通路堵塞,將金融危機變成經濟災難。班是一個低調的人,不容易歇斯底里或誇大其詞,我稱他是中央銀行的大佛,他決心不重蹈他們的覆轍。雖然我們的個性和背景大不相同,但我們彼此互補,他的優點就是我的缺點,他的耐心平衡了我的急躁。在整個危機期間,我們幾乎是在完美和諧的氛圍中工作,而且我們信任彼此。
在當天早上的電話會議上,班、唐.科恩和我都同意, 我們需要明確表示聯準會也願意向我們的市場注入流動性。恐懼正在整個金融體系中蔓延, 特別是在觸及房地產的各個角落裡。由「不合格(nonconforming)」的房屋抵押貸款所擔保的證券,也就是那些沒有房利美或房地美擔保的證券,正在成為賤民票據,沒有人知道它們現在還值多少錢了,所以幾乎所有人對它們都避之唯恐不及。這對那些用它們作為短期貸款抵押品,或根據其價值以樂觀角度來計算出應持有多少資本的金融機構來說,相當危險。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在當天提交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檔案中提到,現在房屋抵押貸款融資是「前所未有的混亂」。房產泡沫的破滅曾讓人感覺像是狂熱的結束,而對房地產相關投資的抵制,現在讓人感覺就像是一場恐慌的開始。
任何危機在一開始發生時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診斷迷霧。你可以識別到嚴重危機發生之前往往會出現的脆弱性,比如資產價格大幅上漲和槓桿使用率急劇上升,但你無法確定最初的市場動盪是健康的調整,還是系統性崩潰的開始,是經濟適度放緩的前兆,還是更糟糕的事情即將要發生。對過熱的市場進行有序去槓桿化可能是一件好事,即使這會讓一些大公司因此而倒閉。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薄弱、虛胖和管理不善的公司讓路給更有活力的競爭對手。創造性破壞讓倖存者學會了紀律,但是,如果恐懼和不確定性獲得太多的動力,健康的調整就可能會失控。你不會希望中央銀行的反應太慢,讓存款戶和債權人進行擠兌,因而引發一連串的拋售。急需現金的公司會不得不在低迷的市場中拋售他們的資產,進一步壓低資產價格,引起更多的現金短缺和更絕望的拋售。一旦這種擠兌和拋售的動態開始,就很難控制,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也就是說,如果中央銀行將每一次騷亂都視為潛在的災難,一有風吹草動就出手相救,那麼它就可能會產生真正的道德風險,會鼓勵不計後果的冒險行為,支撐無法生存的「殭屍」銀行,重新吹脹大泡沫,並使經濟從更高的懸崖上墜落,最終擴大下一場危機的規模。因此中央銀行的過度反應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立即加劇擔憂,而不是緩解擔憂。市場有時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政策制定者表現得好像情況很糟糕,那麼情況就一定是很糟糕。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最好還是退後一步,就像我們在二○○六年九月所做的那樣,當時對天然氣期貨的糟糕押注使一個名為不凋之花顧問公司(Amaranth Advisors)的大型對沖基金破產。這看起來像是一次性的,是不良風險管理的一個特殊受害者,不太可能點燃金融體系的其他部分。事實確實如此。
二○○七年八月的局勢似乎更加危險,更具系統性。我們迅速向美國金融體系注入了六百二十億美元,雖然沒有像歐洲中央銀行向歐洲注入的資金那麼多,但足以發出一個表明我們正在處理此事的訊號。這是中央銀行相當溫和且非常常見在情況發生的初始階段所做的升級,為市場注入了一些流動性。然而,我們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一些同事認為我們太過激進了,因而引發了一場辯論,這讓人想起我們過去在亞洲危機期間,就道德風險所進行的辯論。在十日上午的電話會議上,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Dallas FED)主席理查.費希爾(Richard Fisher)表示,我們正在幫助銀行,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我們「未雨綢繆」,沒有承諾現在提供更多的貸款或在未來採取更負責任的行為。他想確保我們沒有發出任何好像是我們恣意妄為的訊號。
「我認為這不是思考問題的方式。」我說。我們需要發出有現金可用的信號,以幫助解凍班所說已經「全面凍結」的房屋抵押貸款市場,只有這樣做,才不至於讓流動性短缺造成資產被迫拋售,並陷入資產價格持續下跌的惡性循環中,但這也意味著承諾將無條件地提供市場運作所需的流動性,即使這確實讓我們看起來像是在恣意妄為。「你無法在不破壞其基本權力的情況下來做這一聲明。」我說。
費希爾的不安好像預示著我們將要面對什麼意想不到的事。即使在聯準會內部,我們也很容易受到《舊約》和道德風險批評的影響。在危機發生後的一天,已經有一些人認為我們在縱容肇事者。在危機中總是這樣的,我又感到那種熟悉的不祥預感。
我回到紐約參加一場熟悉的策略會議。我記得卡蘿在一次緊張的電話會議中打電話告訴我,蝙蝠在我們開普敦的小屋周圍飛來飛去,嚇壞孩子們了。她患有鈣化性肌腱炎,這讓她的手感覺像被卡車碾過一樣,這種疾病不利於清除蝙蝠或單親養育。我又缺席了,就像我們的孩子還是嬰兒的時候一樣,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很少完全在場,我又是那個回家很晚,兩隻耳朵上都還戴著耳機講電話進門的人。我的弟弟喬納森曾經說過,在家庭聚會上,他總是能從看到我的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是否真的在現場;二○○七年八月之後,我通常都不在現場。
我對未來感到恐懼,比我在財政部應對危機時所感受到的還要糟糕。我知道我們的金融體系槓桿率很高,容易受到群眾心理突然轉變而影響,我不相信我們有應對恐慌的工具,我知道我們還有很多還不知道的事情。
例如,加州貸款機構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oration,以下簡稱CFC)直到八月十五日晚上前不久才出現在我們的雷達螢幕上,當時它幾乎癱瘓了整個系統。
CFC不僅是最大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機構,也是最大的房屋抵押貸款機構,它在二○○六年發放了近五兆美元的貸款,《財富》雜誌(Fortune)將它稱作「兩百三十倍的股票」,這是對它二十年來驚人增長的讚譽。它擁有一家擁有保險存款的中型銀行,為了讓寬鬆的儲蓄機構管理局能作為其監管機構,它已重組成為一家儲蓄銀行,但它大部分的業務還是在房屋抵押貸款市場的狂野邊境,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不受監督的非銀行分支機構。這是一個監管分裂的案例研究:大到足以對系統產生影響,但沒有一個監管機構負責監督其整個機構或者它的潛在風險。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沒有權力監管CFC,但它將會成為我們的問題。
在房屋抵押貸款變得更多元化的時候,CFC 的商業模式全都與房屋抵押貸款相關:發起房屋抵押貸款、提供房屋抵押貸款服務、出售房屋抵押貸款、將房屋抵押貸款打包成證券、交易這些證券,並將這些證券用作再借款的抵押品為其他的業務繼續提供資金。CFC 助長而且帶頭調降全國各地的放款標準,向信用可疑的家庭出售新奇房屋抵押貸款(exotic mortgages)商品。七月下旬,它透露其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拖欠率在三個月內翻了一倍,它的首席執行官安吉羅.莫茲羅(Angelo Mozilo)告訴投資者,現在的房地產市場狀況是自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當投資者看到這些意想不到的損失時,CFC 很快就變成了擠兌的目標。
在二○○七年三月的夏洛特演講中,我曾對提供次級房屋抵押貸款的機構表示擔憂,他們賣掉了所有的貸款,卻不用面對違約的財務後果。一些批評者後來將危機歸咎於這種「從發起到分銷(originate-todistribute)」的模式,放款人因為沒有「參與其中」,所以他們擔心借款人長期信譽的動能有限。這是一個問題,CFC在當中大量參與,但它卻沒有充分分散它所產生的風險。這就像一個毒販,因擁有大量的毒品而變得興奮。它的主要問題不是糟糕的動機,而是糟糕的信念,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房地產價格會永無止境的往上飆升。
書籍基本資料
- 分類:基金外匯總經投資
- 作者: Timothy F. Geithner
- 譯者: 陳季伶
- 出版社: 寰宇出版
- 出版日期:2023-07-31
- ISBN:9786269683543
- 商城書號:F479
- 規格:平裝 /578頁 /25開 /單色/初版
加購商品
-
加$360購買定價:$480元 2017-2019投資大進擊:全球趨勢專家首次揭露一輩子一次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外匯交易精論
-
加$210購買定價:$280元 3天搞懂中國投資:搭乘「貨幣直航」,直掏13億人腰包,錢滾錢
-
加$280購買定價:$400元 散戶升級的必修課
-
加$182購買定價:$260元 點時成金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掌握台股大趨勢
-
加$266購買定價:$380元 《交易大師》操盤密碼
-
加$210購買定價:$300元 賺遍全球:貨幣投資全攻略
-
加$240購買定價:$320元 我如何在股市賺到200萬美元(經典紀念版)
-
加$225購買定價:$300元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窮理財法」提早
-
加$600購買定價:$800元 賈伯斯傳:Steve Jobs唯一授權 (最新增訂版)
-
加$338購買定價:$450元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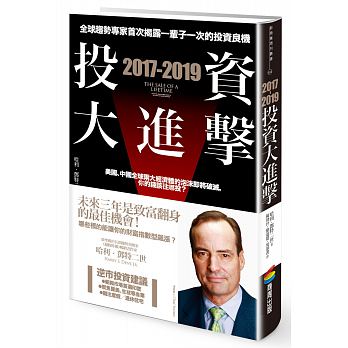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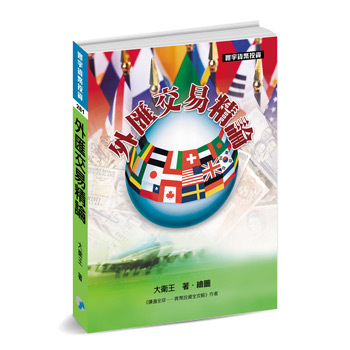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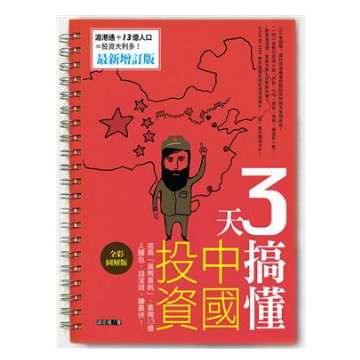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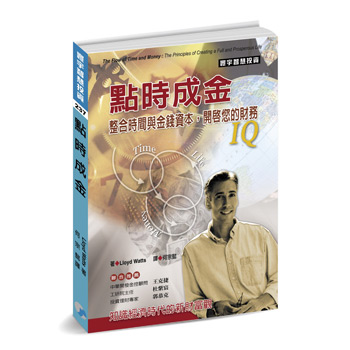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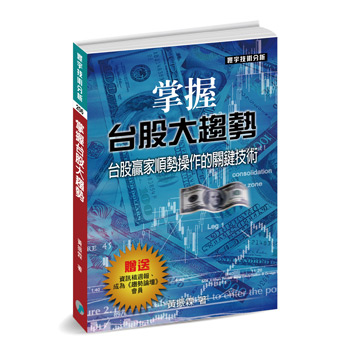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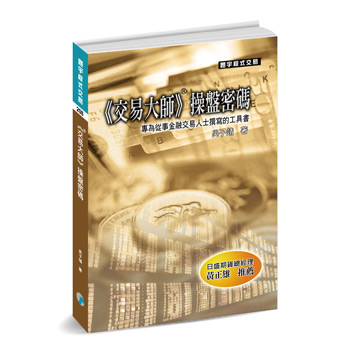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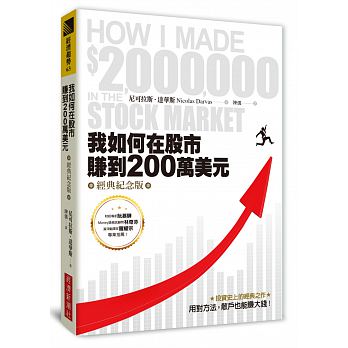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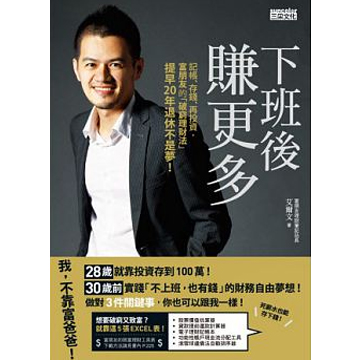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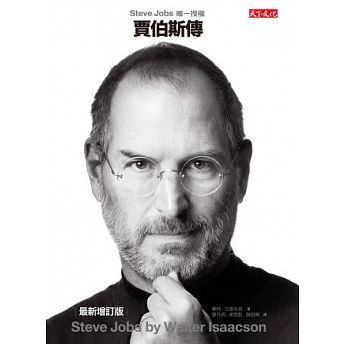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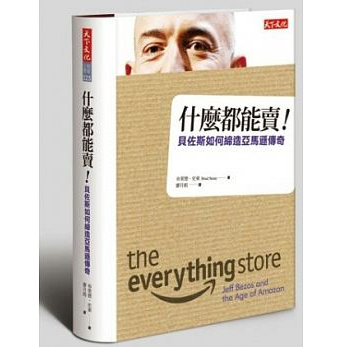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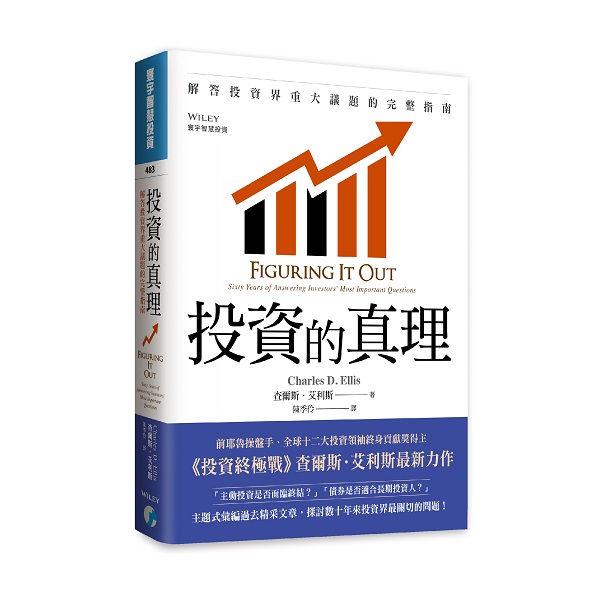



 Search
Search